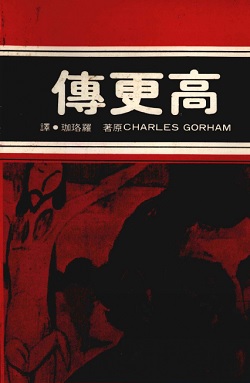第1章 第一章
第一章
一
画商比尔.马甘微笑着对他的顾客说:当然,我曾经说过你有天才,他尽量使声调缓和,以一个业余画家而论,你的作品可以说令人相当吃惊,但是,如果要我替你卖画,我亲爱的高更,那又是另外一码子事。
既然你是一个画商,你就应该想办法替别人卖画。保罗.高更说。
高更是一个高大、黝黑的人,强健有力,流着拉丁血液的头颅,给人一种野兽的感觉。他穿着一件染满油漆的斜纹布外套。
告诉我,高更,你离开股票行业有多久了?马甘问。
差不多两年了,高更说:这两年我没有休息过一分钟。不论在巴黎、在诺曼第,或者在卢昂,我从来没休息过。
他凝望着一张风景画,那是四个月前,十月初秋在卢昂画的。
他看着自己的画,耸耸肩膀。
我以为这张画至少可以看出一点点我的天才。他坦白的说。
画倒是一张好画,画商表示同意:和我堆在地下室里毕沙罗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你晓得,毕沙罗的画是从来就卖不出去的。
当高更还是一个仅在星期天作画的银行家时,毕沙罗曾经做过他的老师。所以在高更的画中,充满了毕沙罗的味道,但是高更是最难承认这项事实的。他正想开口替自己辩护几句,画廊的门铃响了,响出一阵子警告的声音。
对不起,高更,比尔.马甘说。他转身去招呼一个穿着华贵俄国黑貂披肩,形容枯槁的妇人。在她身旁有一个颜色苍白,比她至少年轻二十岁的青年。
郡主夫人,比尔.马甘说:大人。
高更笑了笑,这种一八八四年法国宫廷式的称呼早已经过时了,只要你有钱,在这种场合中,钱仍能和这类称呼相得益彰。
高更相当注意的聆听他们谈生意。比尔.马甘拿出一张彩色鲜明的画,外面镶着价值三百法郎包金的画框。这张画是极粗俗的,标准妓女文学笔下的产品三个高大的粉红色裸妇横躺在一丛毫无质感的灌木林中,四周围绕着一群在结婚蛋糕上做装饰用的小天使。
高更转身去看他从卢昂带来的那张风景画,在它和这张粉红色垃圾之间,他无法找出一点相似之处。高更是属于当时所谓的现代派的。他们受不了关在死气沉沉的画室里作画,所以只好跑到郊外空气畅通的地方。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是一些叛逆者,因此,他们必须接受一般人对新作风的冷嘲与热讽。
当比尔.马甘作完生意,将郡主夫人打躬作揖的送走之后。高更问:告诉我,马甘,你出售那堆垃圾是照英尺算的还是照带框子的重量算的?
要使一个刚赚钱的人扫兴似乎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尔.马甘笑起来,摩擦着双手:管他是照码算还是照公斤算,总之画是卖出去了。他说:我虽然不反对你们的现代派,但是我要填饱肚子,就得供应社会上一般人所需要的艺术品。
高更凝重的看着这个身穿斜纹西裤和黑色外衣的画商。
一般人,高更轻蔑的说:如果那张画能代表社会上一般人趣味的话,我只求上帝保佑我们法国了。
高更走进比尔.马甘画廊后方,端详着那张刚售出的粉红色油画,它的作者是全法国最成功的画匠波格罗。
波格罗,他说:总有一天这些画会全部请进妓女户。马甘,做做好事,把它反过去朝着墙放罢。
比尔.马甘大声笑着,把那张画反过去。
事实上,他说:如果你的预测没错的话,这张画将要放在你想像的那类地方。
高更摇摇头。
大多数的妓女都是诚实的,他说:可是像刚才那位女士,你花钱花在她身上都不值得。
他再次端详着自己的那张画,微微的感到一阵失望。但是不可否认的,画中的确表露了某种才气,就是一个白痴也看得出来。
马甘,我必需卖掉几张画才行。他说:我非常需要钱,美蒂又生了一个孩子。现在我得养活七口之家,但是我却几乎一文不名。明天我总得想法子塞饱他们的肚子啊!
比尔.马甘非常吃惊,他一直以为高更是一位艺术品搜藏家,是个颇负盛名的击剑家和在星期天画几笔的股票商人。他以为高更穿着棉布外套仅是增加点艺术家气质而已。
你别开玩笑了,高更,他说:我不是想要管你的私事,你不是一向都是春风得意的吗?总不至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吧?
从前虽然不太差,高更懊丧的说:一年可以赚四万法郎,当然我也有一些积蓄,但是早就坐吃山空了。
怎么搞的?比尔.马甘问,他仍然记得两年前的高更,穿着当年巴黎最好裁缝师傅裁制的衣服,偶而买几张马奈和塞尚的画,在股票同业聚会的豪华餐馆中大请其客。
简单之至,高更说:头一年我们住在巴黎,照以前的排场过日子。用了两个女仆再加上其他要命的开支。后来感到稍微拮据了些,就把家搬到卢昂,你知道,那里的生活程度比巴黎低很多。
真不敢相信。比尔.马甘叽咕着。
现在我已经濒临绝境了,我非要卖出几张画不可。
这类东西是卖不出去的,比尔.马甘指着高更从卢昂带回来的那张风景画说:现代画在市场上非常不吃香,就是某些成名大师的画也没有销路,何况一些籍籍无名的人了。
总有人拿钱出来买画,高更顽固的说:总不见得人人都喜爱那些肮脏的波格罗作品吧。
有钱人买那些他们看起来觉得顺眼的画。比尔.马甘说:现在他们要买画来配路易十五王朝样式的家具。如果你真想把画卖出去的话,我奉劝你不如到罗浮宫去临几幅拉飞尔或波西尔的画,我也许可以给你找到一两个主顾。
我是一个画家。高更说:我不干这些把死人从棺材里抬出来的勾当。
于是,他要求比尔.马甘把他的那幅风景画存放在画廊里,碰碰运气。然后他就走出来,横过狭窄的,鳞次栉比着画廊、钱庄的拉飞街。距比尔.马甘经营的画廊不远处就是高更从前工作的白庭公司。他在那里停了下来,看看公司门口的几根黄铜梁柱,散发着冷而硬的光辉。然后,他静静的离开那里。
比尔.马甘曾经是他最后的一点指望,其他的画商如拉文、杜朗、哥培等都是一丘之貉。我堆了满屋子塞尚的画,杜朗曾经告诉高更:我还不能把它们当旧帆布卖出去呢。
我的画廊地下室全塞满了毕沙罗的作品,拉文也说过,我总不能将它们卖给肉商用来包肉吧。
哥培更干脆:根本就没有人要买现代画。
他们统统错了,高更想,总有一天,现代画要把那群粉红色的裸女赶到地狱里去。不管怎样,将来总有一天,总有那么大快人心的一天。可是现在,他必需想法子弄点钱,只要有那么一点钱就可以使妻子的眉头开展。但是他应该去求谁呢?上个月,他曾经向他的姐姐玛丽讨了一百法郎,同时带回来她的唠叨她再三强调这点钱是为了救济他无辜的妻子儿女。玛丽是很富裕的,如果他再次去向她乞讨,她一定会赏赐他几文,但以他现在的心情,他是无法去向她低声下气的。于是他决定到蒙马特区去碰碰运气,那里是他朋友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也许碰巧有人卖了一幅画,可能会给他五十法郎。
二
他走到所有现代画家聚集开怀畅饮,高谈阔论的新雅典娜咖啡屋,那里可说是一个俱乐部,在那里估计一个人的价值并非以钱的多少来计算,而是以他对艺术热爱的程度来衡量的。
是一个相当寒冷的十二月天,新雅典娜弥漫着木炭和葡萄酒的香味。玻璃窗蒙上厚厚的一层蒸汽。一张专为现代画家预备的桌子上坐着开米尔.毕沙罗、底加斯和年轻的劳特列克,高更穿过人群,笔直的向那张桌子走去,搬了一张椅子,坐在毕沙罗身边。
一杯苦艾酒,他向侍者说。然后看着对面的劳特列克,后者的肘旁堆满空了的酒杯:看来我们年轻的朋友酒瘾可过足了。他说。
当高更要的苦艾酒端上来时,他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喝光它。他一直喜爱苦艾酒,但是和令毕沙罗满足的、便宜的红酒比较起来,他总为自己的奢侈感到内疚。当他告诉比尔.马甘他连明天的菜钱都没有时,他是有一点故意夸大其词,但也离事实不很远。从玛丽那里借来的一百法郎已经所剩无几了。他根本不应该把钱浪费在苦艾酒上,或在新雅典娜胡混。他应该坐在开往卢昂的火车上,回家告诉妻子,他对出售自己的画,实在无能为力。
他喝完了酒,再要了一杯,神经质的凝望着挂在桌旁横梁上的油灯。
今天你倒是安静得很,高更,劳特列克说:是喝醉了还是倒楣了?高更居然不讲话,怎么?生病了还是又爱上什么人了?不然又是便秘了!
闭上你的嘴,小丑!高更说:今天晚上你竟敢和我开玩笑。
劳特列克的跛脚虽然藏在桌子下面,但是它们却赤裸裸的根植在他的心中。他的脸突然变了颜色,显出一阵子受到伤害的痉挛,然后,他就开朗的笑了起来,轻松的说:只要你高兴,我就闭嘴,不过,如果你需要灌肠的话,我介绍你一种
不要去惹他,亨利,毕沙罗对劳特列克说:你惹火了他当心他砸桌子。毕沙罗是一位温和的人,有满腮义大利式的胡须。他伸出手臂围住高更的肩说:什么地方又不对劲了?保罗,看起来你真像要砸掉什么东西似的。
我刚从一个画商那里回来,高更说:请你们原谅我的坏脾气。
画商!毕沙罗摇摇头说:他们打的主意就是尽量用低价收购我们的画,然后一心一意的把我们饿死,最后再用高价把我们的画卖出。
我倒是一点都不在乎,高更气愤的说,点燃了一支香烟:主要的是美蒂和孩子们,他们从来就没有受过穷。
女人和孩子天生下来就不该受罪的,底加斯说,他眨眨那藏在蓝色水晶片下视力衰退的眼睛:不过,两年前当你辞掉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曾经警告过你。
我一辈子在画,也一辈子欠别人的钱。毕沙罗说。
看来你们是在怪我打错主意了,其实不然,现在,至少我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画家,我在沙龙开过展览,也参加过独立画会的展出。其实,当我从海军退伍下来就进入银行界也是极偶然的。
没有一个人怀疑你的才气。底加斯酸溜溜的说:只是怀疑你的恒心。成功是需要时间的,高更,但是你却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并且,你也不再年轻了。
我今年三十七岁,高更说:而且没有满腮白胡须,何况无论在床下或者床上,我也不需要用白胡须来帮忙。
他喝光了苦艾酒,再要了一杯。当第三杯酒喝完时,高更开始觉得浑身舒泰起来,整天他感受到的刺痛渐渐模糊了,他开始遗忘比尔.马甘及其他的人,也忘了远在卢昂的妻子儿女。他倾斜着身子,像一个图谋不轨的人一样,高谈着艺术。他全身溢满了力量,这是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的。于是大家围上来听他大放厥辞。他滔滔不绝的讲,意兴飞扬。甚至劳特列克也沉默着,聆听他说话。
夜深一点,其他的画家们也来了,秀拉,他的画是用点构成的。马奈戴着一顶高帽子,席芬尼克和高更一样,从前也在银行界服务。高更忘了时间,不知不觉的就把最后一班到卢昂的火车错过了。
到我家去歇一夜好了,席芬尼克说:我画室里有一张长沙发可以凑合一下。
席芬尼克是一个矮小戴着眼镜的人,他有一个瘦削的妻子。在巴黎郊区孟托乡赁屋居住。
你真够朋友,席芬,高更说,因为喝多了苦艾酒所以口齿不清:而且你也比我聪明,居然能够想到把所有的钱买公债,堵住你老婆的嘴。
席芬尼克耸耸肩膀,他讲起话来仍有亚沙丁地方的乡音:如果我有你的那份天才,保罗,我也会像你一样破釜沉舟。他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百法郎塞在高更手中:不要为这点钱操心。他温和的说:虽然我自己的钱也不多,只要我有,我很愿和你分用。
当席芬尼克夫妇熄灯睡觉之后,高更在那间狭窄的画室沙发上辗转反侧,难于入睡。他的生命并非为了受挫折而存在的。两年前,一切事情都是那么顺利,事业、爱情、战争,都得心应手。他一直相信他有成功的本钱。可是现在,他为自己的贫穷感到羞耻,为自己成为朋友的包袱感到羞耻,更为了明天回去告诉妻子他已经一筹莫展感到羞耻。
三
第二天下午,高更搭车回到卢昂,一年前,他充满了希望来到这个地方,现在,他心中却填满了对此地一景一物的厌恶卢昂代表了整个高更所憎恨的中产阶级。
高更对自己昨夜的宿醉感到惭愧,为了省下一笔车钱,他就从车站慢慢步行回家。在他租赁的那栋小鸽子笼前,他的小女儿安莉妮独自在冷风中嬉戏。她身上穿了一件蓝里泛白的短大衣,她已经靠它度过了三个寒冷的冬天,现在已经小得紧箍在双肩上。再过几天,圣诞节来临时,她就满八岁了。
小乖乖,在这冷风里妳马上就会冻僵的!高更说着,把安莉妮抱起来,并且吻了吻她冻红的两腮:为什么妳不在屋子里和别人一起玩呢?
一定又是为了得罪美蒂而被赶了出来。他想。美蒂对安莉妮总比对其他男孩子们严格些,也许是因为高更最宠爱安莉妮的缘故吧。
安莉妮紧紧的握着爸爸的手,他们一同走进屋子里。其余的孩子们围坐在厨房桌子四周。最大的亚米正在看一本书,克罗文和约翰两人正兴高采烈的玩着几颗残剩的棋子。当高更进来的时候,除了亚米仍然丝毫不动声色的看书外,其他两个男孩子都站了起来。高更俯身吻了吻他们。
你妈妈呢?高更问亚米。
和小弟弟在楼上,亚米冷漠的说:他又生病了。
亚米又回到他的书本上。有时候,高更很想纠正一下他的言行态度。可是想了想,也只得放弃这种努力。亚米已经十岁了,一个十岁的孩子有理由怀恨自己的父亲把家庭弄得一贫如洗。他现在没有零用钱,住在这荒凉的小镇上,和在巴黎时的生活有天渊之别。这些理由构成高更对他的容忍与原谅。高更无可奈何的摇摇头,踏上通往楼上的那条阴暗狭窄的楼梯。他和亚米从前相处得并不坏,他曾经教那孩子糊纸盒子和做模型船。可是现在,亚米好像恨透了他。
高更小心翼翼的推开门,看见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小保罗。她坐在摇篮旁边,暗淡的灯光将她的侧影温柔的映在墙上。他们结婚已经十一年了,直到现在,他仍然为她的美丽感到惊心动魄。正如第一次他见到她,挤过满屋子的人群,他向她走去。
美蒂,他轻柔的说:他怎么样了?
她转回头,举起一个手指按在唇上,垫着脚尖离开摇篮:他刚刚睡着,她低声的说:他醒时会好得多。只是他的身体太衰弱了,保罗,而且这样阴暗潮湿的房子对他太不适合。他们回到自己的卧室,高更忧愁的坐下来。他感到极度疲倦,而昨夜的苦艾酒使他头昏目眩。
跟着他们脚步来临的唯有阵阵的不愉快。
开始并不成功,他说:杜朗、拉文、比尔.马甘,没有一个人看得上我,照他们做画商的人来说,我们是活该挨饿,活该下地狱的。
美蒂坐在一张摇椅上,她曾经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女人!现在,她脸上已经出现了细微的皱纹,满头的金发已经变得枯黄。她是一朵养在温室里的娇花。他想,她不应该受到风吹雨打。
你拼命画了一年,可是一张画都卖不出去!她说。
是的,一张都卖不出去。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他说:我需要时间仔细想一想。
他们为你保留了银行里的职位。她提醒他,正如一年前他们由巴黎搬到卢昂时她一再提醒他一样:他们不能一辈子把位置给你留着。
我不能再回银行!他说:我现在是一个画家了,美蒂,不管是好是坏,我总是一个画家。
我们总不能够依靠空气过日子,美蒂不耐的说:假如你赚不到钱,最好能去借一点。
我现在真是告贷无门了,美蒂!他说:玛丽也许会赏我们一点,但是又有什么用呢?我也不愿去求叔叔,看他推三阻四的脸色。而且,他死后,钱迟早是我们的。
我们总不能活活的在这里等他死掉!她说:我们总不能让孩子们每天挨饿,保罗!
席芬尼克给了我一百法郎,我们省着用几天。
一百法郎!她说着走向屋角的书桌,打开抽屉拿出一叠帐单。保罗,你张开眼睛看看!她说:三个月的房租、杂货店、肉店、面包店、牛奶的欠账。我坦白的说,再这样下去,我受不了。你离开银行时不是曾经告诉过我,我们绝不会弄到像毕沙罗、席芬尼克那样的地步。你说:不要担心,美蒂,我们会保持原状的,要变也只有愈变愈好!可是现在,你看,保罗,我们连他们都不如,我们简直是乞丐,保罗,我们简直就是乞丐!
妳是对的!他说:妳是对的。
我是对的,你说,可是你打算怎么办?难道你真要关在画室里画那些永远没有人要的画,而眼睁睁的看着妻子儿女饿死不成。她的声音因为发怒而提高了,杂着更尖锐的丹麦口音: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保罗,我嫁给你的时候,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可是现在,你简直毫无理性!
他站起来走向窗口,看着窗外溶溶的暮色。
我不怪妳,美蒂,他背向着她:当我们结婚的时候,妳一点都不怀疑我会愈来愈有钱,就好像别人愈来愈胖一样。但是我告诉妳,妳也不能怪我。我是一个画家,我活着,就要画。我画,就好像别人要呼吸一样。不管妳怎么想这是一件不可变更的事实。只要一个人真正掉进这个泥沼里,他终生都爬不出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美蒂!
一阵难堪的沉默横亘在他们中间。然后,美蒂冷静的说:保罗,我们一定得想个法子。这种生活是不能再过下去了。假如你不能回巴黎银行,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
什么地方?他仍然望着窗外。
回我哥本哈根的娘家。她坚定的说:在那里,至少孩子们可以吃得饱,穿得暖,而且还可以上学校。
哥本哈根!他说:窄得令人不能呼吸的哥本哈根!我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法国人,我到哥本哈根去做什么?
美蒂尖刻的把头抬起来。在心底,她依旧是一个丹麦人。十二年在法国的婚姻生活仅仅使她的北欧冰冻式道德观在表面上溶化了一点而已。
你可以像在这里一样的画画,她说:不过,为了面子上过得去,你可以做一些不妨碍绘画的工作。
在她的声调中,有一种尖锐的轻视与不满。这是危险的信号。高更只得从他所站的窗子走开。
你不会是认真的吧!他说:我们怎么可以离开法国?
我们怎么可以留在法国?她问:我是百分之百的认真,保罗,不管你走不走,我是决心要回去。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孩子们为了你一个人的沉沦而受罪。
我是一家之主,他愤怒的嚷起来,假如我不答应,你没有权利把孩子们带走。
依照法律,我当然没有权利,她安静的说:但是我,了解你,保罗,你不是一个天性残忍的人,你不会忍心让你的冥顽不化毁了我们一家。
高更望着外面泥泞的雪地。她是对的。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全家人饿死。去投靠她的家人虽然是一件奇耻大辱,但是他不能放弃自己尚未开始的艺术生涯,手中捧着大礼帽,然后爬回股票事业。
上帝保佑我,美蒂,妳是对的。他低着头,感觉从来没有如此羞耻:我们到丹麦去,我们全家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