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夕阳是一阵光雨,洒落在林捎,闪着昏黄、青蓝的幻彩,一抹紫黄色的晚云横卧在远天,使整个大度山的黄昏都染上一种特殊的光彩。
南森默默的生在一座石桥的桥栏上,朝远处凝望着。他郁郁的孤单的影子,落在多石的干河的河心。
丛丛的相思树,排排的真凰木,摇曳的尤加利,呜咽的马尾松,都在一层上了釉的薄暮光景中包围着他,使他有些存心的不快活;一部份是因为在台北那座大城里挤惯了,不习惯大度山的这种空旷,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该是眉珍没能够依照她的意愿,跟自己一道来读这所学校,她因为家境的关系,到最后决定辍学了。
事实上,像眉珍那样有抱负的女孩子,是应该像一只鸟一样的飞跃在这红土小径上,在这块宽广深邃的地方展开她青春探寻的。
他跟眉珍认识,整整四年了。
他是个很敏锐的青年,常常祈盼着很猛的吞食新的如识,而不耐在课堂上温温吞吞的啜吸。故而,傍晚放学时,逛旧书摊就逛成了习惯,眉珍跟他同在一个学校里,他却是因为逛旧书摊才认识她的。
她是台北牯岭街附近,一家藏书极多的书肆主人的女儿。和她家那种灰黯多尘的背景相对照,她的脸总显得太白,衣衫也总显得太干净了。在最初的印象里,仿佛她是一只抖着翅的燕子,就要从那浓烈的阴黯里直冲出来似的,尤其在她笑着的时辰,可以看出她在孱弱撕文的身体中,有着一股弹靱性极强的野性。
四年当中,他不知多少次踏进那座书肆,翻拣着一架架蒙满灰尘的书籍,安德烈.纪德,杰克.伦敦,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雷马克,王尔德,莎士比亚,成千成百册能够照亮人心的文学作品,都多少带着一份千古圣贤皆寂寞的味道,了无怨色的,静静的蒙尘。他却感觉到这些曾被人扔进垃圾桶,或是捆为废纸出卖的书籍,比那些下巴松弛成威严状,一踏上讲台,照本宣科完毕之后照例穷打哈欠的老教员要亲切得多,也最能满足他近乎贪婪的汲取的欲望。
当然,他常常饿着肚子,把早点钱节省下来,尽量的收买了一部份自己特别喜欢的书籍。她呢?也许因为看书不必花钱,或者在拣选出一些新书时,总希望先看完了再卖出去,总之,她总是在略显昏黯的灯光下面,手不释卷的看着,看着,还做着密密麻麻的笔记。
灯光太黯了。他心里这样担心着,嘴里就说了出来:桌上该添一盏台灯的。
她望着他,从校服上认出是同校的同学。
习惯了,倒不觉得。
他翻翻她所看的那册书,笑着说:
将来打算进中文系,我猜想。
为什么?她淡淡的反问说。
猛啃文学书,将来妳一定打算做作家。
她阖起书本来,很正经的微笑着:
合逻辑吗?你不妨数一数看,当代配称为作家的,有几个是念中文系的?挖了四年古,深不深,浅不浅,只怕摆旧书摊子,都糊不了口。
他一时语塞了,好在灯光黝黯,她不会注意到胀红的脸色。他没想到,以她那样看上去沉默文静的女孩子,轻描淡写几句话,竟说得这样锐利?一针见血的道破当前教育方式上崇古薄今的缺失。这丫头也许真的是读旧书本儿读出不寻常的学问来了!
事后证明他的猜想是对的,眉珍自小就跟她父亲拣选书本,穷啃那些被一般人冷落甚至舍弃的书本,对于这种两人相同的爱好,她至少比他多出五六年的道行。她啃过的旧书,不仅是文学的,还包含着哲学的,历史的,社会学的,一部份自然科学的,那些被社会认为是只配包里零食和杂货的书本,就那样的充实了她,使她比更多大学生更懂得思想。
他跟眉珍就这样熟识起来了。
联考之前,他找过眉珍,想跟她多谈谈,一方面解除自己内心那种迷迷离离的困惑,一方面想借此增强彼此将选取学习方向的信心。两人散步到不远处的植物园去,那天的黄昏,正像眼前大度山的黄昏一样,只多了一层由都市的尘烟结成的障幕,光景就比较黯淡得多,也沉重得多了!
他们在多曲折的池边的石径上慢慢的踱着,两人谈了很多天南地北的事情,谈起那些专卖新书的书店,只是抹了厚粉的东施和无盐,谈到一部部该得最佳勇气奖的当代巨著,既浪费了纸张油墨,又浪费了印封面用的颜色,谈到一位时作权威状的作家在学校里所作的一次不如所云的演讲,又谈到日渐艰难的旧书摊的生意两人都会出声的笑出来,但又觉得内心常被那种并不代表快乐的笑声所牵痛。
最后,还是他先提起横在眼前的联考。
眉珍,妳的志愿打算怎样填?我是说选择学校的话他故作轻松的说。
而她却轻轻锁起了眉头。
你是知道的,黎南森。她沉吟一会儿,低声的,缓缓的说:一个靠开旧书店维持生活的人家,我父亲老了,最近又闹病,他虽说一直要我去参加联考,我心里可真乱得很,想罢,又烦人,不想罢,又不成。
书总是要念的,像我们这种年纪,他说:妳明知准会考取的,要是辍学在家,又能做什么呢?
她抬头望望天边楼齿上挑着的,浑浑浊浊的霞光,又低下头去,看着池里的莲叶,叹口气说:
不是说痴话,真的,我很想离开台北远点儿,去念念大度山上的东海!虽说私立学校收费贵些,但那边工读的名额不少,将来自己勤一点,苦一点,也不会浪费到哪儿去,不是吗?
为什么妳偏爱东海呢?他说:我很想听一听妳的意见。
这一回,眉珍的眉头略略舒展了:
有人告诉我,那里的学生走在路上,可以自由自在的吹吹口哨。有人还告诉我一些旁的事,此如梦谷、土地公、啼明鸟你不会笑我的怪想法吧?我想,人进大学了,除了念书,还该念念感觉,东海会有那种感觉的。认花、认树,认那些石头,多有意思。
选系呢?选系打算怎样选?他说:我猜妳还是会选中国文学系的,开旧书铺方便。
不,我会选社会系。
社会系?
是的,她认真的说:我想过这问题,正因为我喜欢文学,我才要选社会系。要不把这社会弄个清楚,看个透澈,将来写文章打哪儿落笔呀?只写椰子树下谈谈情,电影院里说说爱,就算交了卷了吗?
多值得人去深思的言语!那确曾是由眉珍嘴里说出来的,他严肃的沉思默想过,自己也该选社会系,而且得多旁听一部份历史课程。
好,他最后站起身,挺胸握握拳: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只填一个志颐,去念念那个可以吹吹口哨的东海,念梦谷、念土地公、念啼明鸟,念整座的大度山和我们自己的梦。
对了。她说:那是书本之外的课程,一样是必修科,算学分的!
年轻人总那样容易受情绪的感染,一谈到梦想,就很快的兴奋起来,满脸都是焕发着生动愉快的光彩。那天晚上,他就安心的回去准备功课,等待着联考,他曾细细的摹想过将来,将来跟眉珍在一起,怎样的互相切磋砥砺,精研学术,同度大度山那四年的岁月
但,那只是一场碎梦罢了!
和眉珍相识以来,两人相处得那样投契,互相敬慕,彼此尊重,一幕一幕的情境都影画般的在眼前陌生的暮色里浮现出来,因为如今和眉珍分别了,这段真纯的友谊,更使南森珍惜着。
她没能如愿参加联考,因为在联考前夕,她的老父,那旧书肆的老主人去世了。他不敢想像眉珍内心是怎样的痛苦,怎样的悲伤?她是那家的长女,她父亲死后,照顾店铺,负担全家生计的担子,一股脑儿都要卸在她一个人的双肩上,当然,她得辍学,也就是说:大学之门,已经在她眼前关闭了。即使她本身无怨无尤,勇敢的承担困陷她的噩运,而南森却不得不为她抱屈,为她不甘,为她分担一份抖不脱的苦楚。
归巢的鸟雀碎语着,掠过转为灰紫色的天空,一群一簇新来报到的同学,在每一条红土路、石板路上徜徉着,从他们泡沫似的流散的语音里,听得出他们的欢欣和雀跃初次出巢飞翔的幼鸟所有的欢欣和雀跃,但他没有动,他落在干河心的乱石上的影子,已淡得似有还无了。
层层的林木黝黯的影子落进他的心里,他仿佛能听得见轰轰滚动的南下车轮声,昨天夜晚,和眉珍告别的情境,依然像车轮声一样的凄厉,绞痛他的心腑。
落着暴雨的夜晚,他摸到眉珍家那条短巷里,廊下的昏灯照亮了冷冷清清的白纸贴儿,书肆关了门,在夜晚的雨里,分外显得破落、寒伧。他原准备了一些安慰的话,一旦走近那座略显歪斜的克难房子,心里便乱得像滚散了的线球了。
他轻轻的叩击那扇虚掩的门,应门的正是眉珍,雨点敲打着残缺的铁皮廊项,发出咚咚的噪声,廊影挡着门端,屋里一片黝黑,眉珍的脸廓只是一团隐约的白,分不清模糊的眼眉来。
是南森?还是她先说话,她说:这么晚了,顶着大雨跑来,快进屋来生罢。
他摇摇头,大声的说:
明天要去东海报到了,不用啦。我我只是来看望妳,也算辞行罢。
檐漏滴落在他的衣领里,一点一滴的冰凉,雨声噪乱得使他非放大喉咙说话不可。而他所说的,并不是他要说的,即算有一整夜的时间呢,他也无法把内心纷乱的言语,逐一的说给她听了。
歇会儿嘛,南森。她说:该祝你一帆风顺。
谢谢妳,眉珍,我还得赶整着行李,我这这就得回去了,再见。
再见,别忘了来信
他迅速的掉转头,仿佛忍痛割断什么似的,奔离那条短巷,在巷口回头,门已关了,黑黑的夜,清冷的灯勾勒出一排不很规则的檐影,把眉珍锁压在那里了!然后是大度山,是这石桥,这旱溪,这重重林木托着的黄昏,这样宽旷的天和地,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多容纳一个原可以高分考取的眉珍?
晚风起了,吹动他略显蓬乱的短发,黎南森从石桥边站起来,朝宿合那边走过去;黄昏已过,一种山间特有的夜气,像雾般的,从草原的尽头,从深邃的树林里,从那些醉红的泥路上,轻轻缓缓的飘腾起来,把人给围着,托着,那柔白色的氤氲,逐渐的说罩了广大的校园,拥吻了在林荫大道上漫步的少女,一切都显得温柔。
蓝里带青的路灯,一道道迷蒙的冷霜似的,照着这大度山间的初夜。假如眉珍在这里,她会有着怎样的感觉呢?不也像一群穿梭在林野间、彩蝶似的女生那样笑语经盈么?初初展放的青春,汹涌奔流的生命,各藏着丰沛的情感,爱着也憎恶着,学习着也梦想着,踏进校门的热望,将被这里展露的美,提升而飞扬,谁说这不是未来中国年轻一代的原始力量?
即使眉珍没能如愿,小小的挫失也不会把她压倒的,她并不是一般柔弱的女孩子。自己如何呢?总不能为着这个,就认真的忧郁起来,自己应该无忧无虑的敞开心怀,选读社会系,是眉珍和自己共同认定的目的,那么,就这样猛锐的开始罢!
照样的性格起来!啃。南森心里有了这样的转念,胸脯便高挺起来,他的日影子,穿过薄雾游漾的林荫,像一颗发亮的、跃动的星,有一股本能的,年轾而野性的光芒,被覆在他平稳的两肩上。
南森的影子被路灯嬉弄着,一会儿缩短,一会儿又拉长。现在,他登上了寝室的楼梯。他虽被分配到新生宿舍楼上的二○四室,但还没见着其他三个同寝室的室友。
谁知那三个家伙是谁?他在喉管里咕噜着。
这一点是顶重要的,他也想到过,假如爱早起的碰上一位爱晚睡的,爱清静的碰上一位爱吵闹的,有气管炎和哮喘病的碰上猛吸烟的,患失眠的碰上穷打鼾的,那都会产生格格不入的窘况,使彼此都像进了阿鼻地狱,假如是这样,那可就惨了!
他轻轻推开门,又砰的一声,把黝黑的东海关到室外去了,他这才带着很不介意的笑容,转身面对着同室的那三个。一个高高瘦瘦,很有几分排球头排选手味道的家伙,全身躺在椅子里,有节奏的摇着,很老练的吸着烟。另一个头靠着床头的横板,把两只脚高高的说放在床杠上,弓着背,隔着袜子捏着双脚,他的个子不高,却粗壮得像是举重选手,他的脸色黝黑,有些像拿斧头劈出来似的,多棱多角,络腮胡子虽刚刚刮过,却仍倔强的青成一圈儿,大有野火烧不尽的意味。第三个躲在一边的角儿上,很正经的看着一本外文书,他的长相很秀气,英俊,但一点儿也不潇洒。
黎南森倚在门背上,三个同时抬头,各瞟了他一眼,表情各异,但都没开口讲话,那眼神既说不上冷漠,又说不上热烈,这寝室就该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了,大社会分拢来的小社会,算是东海给他的第一道题目。
他知道,东大的寝室分配,大部份是同年同系为原则的,这三个想必是同伙了?他不知为什么,也陷进不甚自然的沉默里来了,盯盯高个儿手里的烟卷,又看看窗外尤加利树的大青叶子,心想:不知从哪儿考来的?背景、性格、心情都不一样,又没有半点交往基础的陌生的脸,真有几分像在荒岛上相遇,渴望拉手又怕对方不伸手的那种焦急味儿呢!
我叫黎南森,台北市考来的,念社会系。他终于打破沉默说:朝后,我们是朋友了。
本人叫高原,喜欢旁人叫我老高,老高仍然摇着那把明明不是摇椅的椅子,用手里的烟蒂接上另一支烟说:咱们是同乡,我是师大附中的,选外文。
苏一雄。躺在床上的有些油条,也许用那种意味掩饰自己的羞窘:我的老习惯,是喜欢捏脚丫,不过,保证不臭就是了。
没有关系,我有鼻塞病。南森说。
三个开了口的,都在一刹那间大笑起来了。只有没开口的那个,只在唇边划了个浅浅淡淡的文雅弧线。
贺良唐。他细声的自我介绍说:嘉义来的。
大概也是选外文?我猜是。南森拖过一把空椅子,两肘交压在椅背上,用骑马的姿势倒生下去,一面轻松的用下巴抵着手背说:我以为,咱们朝后总是要熟悉的,不如今晚上就熟悉起来罢。老贺,你是在闹情绪?
贺良唐羞涩的笑笑,没说话。
老高一面吸烟,吐着烟圈,一面说:
情绪闹不得,那该是闹精神自杀,学问没弄透的时刻,看法,想法,都浑浑沌沌的未必就对,闹情绪才是傻瓜,别介意,贺兄,我无意说你。
像我最好,有什么不如意,搓搓脚丫就过去了!苏一雄说:我是乐天派,所以活得非常过瘾。
他这一说,连最后一点陌生的感觉也被笑声完全的融解了,四个人的脸孔,都生动起来,使原本冷清的寝室在无拘无束中添了一份温暖。南森直接的意识到这小小的社会如今是在活跃着了。
说真的,我报到最早。他说:可是,我闹了一天的情绪,为了一个女同学没能进东海,我真想发一场牢骚。
发罢。老高说:免得闷在心里,会失眠的。
于是,南森就坦直的,把眉珍的事情一股脑儿说了出来,他坚持着说:
假如那个女孩子来东海,她会替大家心里点上一盏灯的,可惜她只能守着那间黑黑的旧书铺了。
事情很感动人,老高带着一付颇有深见的派头,有条有理的指陈说:但这终究是你个人单方面的观点。事实上,不念大学仍能力争上游,并不是悲剧,念了大学,混水摸鱼摸四年,然后靠老子花钱放洋去鬼混文凭,回来吓唬人,那才是悲剧。在这一点上,你犯了诉诸情感的错误,对我们来说,决心摸黑来的,何必要依靠她那盏灯?
当然。可是你得知道,我原来就是发发纯粹情感上的牢骚,无伤大雅可不是?
对!老苏拍打着大腿说:有牢骚才有冲劲,有冲劲才有活力,像它娘一只火车头,轰通轰通朝前跑,才配选读社会系。假如凡事不出头,缩在龟壳里,念完社会系,结果社会还是社会,你还是你,那,书还有什么念头?拿文凭揩屁股,会长痔疮的,我以为,在文凭主义一窝蜂的浪头上,文凭就代表着不通!把不通贴在肛门上,长痔疮难道没有科学根据?
那,你是反学院派,南森笑说:那你何必挤来东海搓脚丫?
谁反学院来?我只是幽它,呃,幽它一默,不过,我得郑重声明:东海例外。
去你的,东海因何例外?
嘿嘿,老苏两眼神秘的转动着:因为本人我在东海!乐天派的人,一向是老太太头上的簪子路路皆通的。他在人忍俊不置时,又加一句:包括肛门。
动力!南森一面竖起拇指说:这就是动力!在中学,那个戴老花眼镜的训导主任,什么都许有,许念书念成近视眼,许代表学校的球队免交作业,许学生把维他命当成花生米,可就是不许有动力!
拿出证据来,快!老苏的巴掌又跟他的大腿过不去了,连拍三下挺响的,那神情,好像法官在问案时手里舞动的法槌: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等日后咱们做一位真正的社会改革家的时候,立刻吁请教育当局,以加倍的退休俸,请这位老花眼回家抱孙子去,甭再留在学校里训而不导了。
证据?太多了!南森说:有一回,我在校园里散步吹口哨,老花眼听着了,招手要我过去,我立正报告,问:主任找我什么事?他说:去,回你们教室拿支粉笔来。我拿了粉笔来,你们知道他要我怎样?他要我在水泥地上划一个圆圈,要我直腿直脚的站在那里头,好像真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决心,把我当成一棵树,硬栽!
不错,老高插嘴说:那位老先生,一定是个死抱着传统,食而不化的复古派,这有个名堂,叫做划地为牢。想当年,姜子牙全在里头站过,像你这样一个高中生,更当不在话下了!
可是我当时抗议说:您怕没弄明白?我没有摘花攀树,只不过吹吹口哨呀嘿,他说:我就是罚你吹口哨,你算是不打自招。我又苦笑说:您知道的,我吹的不是流行歌曲,是是柴可夫斯基的曲子。你们猜他怎么说?他说:我不管什么死鸡活鸡,就是贝多芬念这个学校,我一样不准他吹口哨!
杀天才的学校,老苏说:而且用的是慢刀。
也许你走霉运,碰上这种怪物了。老高说:我们学校从不这样,我想那该是个别现象。也许老花眼心理不正常,譬如特别讨厌音乐什么的。
噢,天晓得!南森耸耸肩膀,扮出一个无奈的神情说:你说他讨厌音乐?有一天,我在武昌街二段,一家歌厅门口过路,穿过一条横排到马路上的长龙,我的手肘无意间碰上一个人,正是那位老花眼训导主任,他推动镜片看见我,故意把脸转开,他在那儿挤票,他对妹妹我爱妳、樱桃树下,口胃蛮大呢!就凭他那样,贝多芬要是咱们同学,一样要在水泥地上的粉笔圈里练腿劲。那一回,我足足站了一个钟头,害得我一年不敢吹柴可夫斯基的曲子。
啧啧,一直没开口的贺良唐说话了:这简直很罪过,要是我,一定受不了!
受不了,转学可以,千万不能跳河自杀。老苏说:前几年,日本青年跳河自杀的风气极盛,多半是像你这样文雅,不多讲话的。
为什么?南森说。
因为,因为老苏搓着脚说:个性内向的人,多半想不开,不懂幽默的妙处。据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联合实地调查的结果,做成一项睡不着觉怨床歪的结论,他们责怪桥身的颜色是黑的,一方面容易使人产生忧郁和绝望感,同时,黑色原就是死亡的象征,好像他们的那些时代青年,都是些薄玻璃瓶,一碰就碎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如今年轻人会这样脆法!南森表示异议说。
别忙,我还有下文。老苏说:我相信,我们的青年人虽也有难处,但却没脆到那种程度,害得日本当局赶快把桥身改漆成橙色和绿色。
嘿嘿,南森说:那,闹恋爱的人就多了!
精神自杀的也多了!
你没有意见吗?老贺。南森说:你们嘉义的柳树很多,你不会为恋爱闹情绪罢?他把头转向贺良唐,希望听听他的声音,但对方摇摇头,仍然不肯说什么,一丝略显忸怩的晕红,又染亮了他的脸。
你究竟喜欢哪一门呢?南森说。
音乐。偶尔也打打网球。
天,南森望着他:你一点也不像网球员。
你全弄岔了,老高掷去第二支烟蒂说:南部六县市软式网球赛,他拿过亚军,他是体育世家出身。
音乐、网球,都酸得很,老苏开始捶捶刚才被他自己拍痛了的大腿和脚,真够他消遣的。
那你喜欢什么呢?
泡密丝。
算啦,老高说:咱们新生,太嫩,犯不着又花钱,又当孝子。
泡垮了,又得闹精神自杀,划不来。
嘿嘿,这种精神自杀,多多益善。老苏说。
四个人的笑声又综合起来,在二○四室里朝外荡开。大度山间温润沁凉的夏夜,很陌生,又很亲和,有一股从没感觉过的自由欢快的气氛,使人有些忘其所以的激奋。南森想过,这也许就是眉珍所指的感觉罢,现在他方领悟到,感觉真的是可以读的。
隔着寝室的玻璃窗,很多明亮的星子在夜空里棋布着,这一百五十公顷的校园,足够每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各写出他们的理想的梦图。他们热闹的闲谈着,甚至有些胡扯着,那并不代表他们不成熟的认知,只是象征着他们内心的欢悦和燃烧般的青春的激情
有关于啼明鸟的传说,倒是由老高先提起来的。
听说大度山上有一种神秘的小鸟,天还没亮,它们就在相思树林里唱着,它们的啼声比黄莺还美。
扯淡,老苏首先反对说:我可从没听说过这种鸟,连名字都有些怪里怪气的,同时,啼明鸟这名字,本身就不合逻辑,连麻雀都是啼明的。
它只是一种鸟,本来就叫那名字。老高说:你不会跟那种小鸟谈论逻辑罢?
那倒不会。老苏说:我宁愿睡睡懒觉。
有人见过那种鸟没有?南森兴致勃勃的问说:早些时,我也曾听说过,不过我实在很难相信,为什么只有大度山的林子里才有这种鸟?
谁见着过它来?老高摊开两手说:只怕谁也没真的见着。据人传说,这种鸟只在黎明之前啼叫一次,它们总藏匿在树林深密的地方,要问,你该去问老东海,总有人比我晓得的更多。
千万不要问那些挑灯夜读,早上贪睡的家伙,老苏咧着牙齿笑说:遇到像我这样的人,嘿嘿,五更天,睡得最甜,甭说是鸡啼鸟叫了,只怕放廿一响礼炮也不会把我惊醒。问那些人,等于白问。
我真不懂,贺良唐打个呵欠说:为什么你们讨论鸟雀,有这么大的兴头?
不懂吗?老高悠悠然的摇着椅子:让我告诉你,聂华苓说过:在东海,大度山黎明前的鸟啼声,该算两个学分。
我完了!老苏说:我毕不了业。它们总不能唱到我的梦里来罢。
它能唱进叶珊的诗里,为什么不能唱进你的梦里?你老兄甭先着急,慢慢的等着罢。
可是你知道,一个乐天派,是难得做梦的。周公那老家伙总是背朝着我。
不要紧,南森说:好在这儿有梦谷,平常不做梦的人,守着那儿的夜,守着那儿的石头和火过一夜,没梦也会变得有梦了
年轻的人总这样,只要摆脱掉过份正经的拘束,他们便会有太多的言语,从心里泉涌出来,无论是快乐的,忧愁的,憧憬的,回溯的,都满蕴着一股明亮的智慧,饱含着一份稚气未脱的真诚。
生命,就这样的展开了,它的方向很多,所有青春的心,都像是盲目疾滚着的马蹄,不知是什么样的不可抗力,驱策着它们,向未来奔驰。它们从这里那里奔驰出去,自会凭借着汹涌澎湃的生命力,求取更高的智慧,更成熟的认知,去驾御他们自己,归向文学,归向新的历史,归向尚待建设的社会,归向更广大的田野和农林,归向一切复兴的行列,有什么样的力量,能阻碍住这种青春心灵的奔驰呢?
南森躺在床上,灯熄了,星光灿然的耀闪在他的眼里,他纷乱的思想载着他的灵魂,也载着他的梦,航着,航着,比三宝太监的船队更加壮阔,比五月花号更具雄图。但也有一些是小小柔柔的,柔如初茁的绿茵,小得能兜在女孩子们印花手帕里,但总很美,在东海,在初来的第一个夜晚,他梦见过眉珍。
他真的梦见过她,在黯色的背景里笑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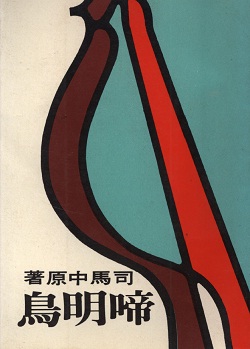
啼明鸟
司馬中原
小说园地
类别- 2023-02-05发表
-
281579
已完结
© www.iabbook.com
按 “键盘左键←” 返回上一章 按 “键盘右键→” 进入下一章 按 “空格键” 向下滚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