眠蚕
天气虽是暮春,说热就热起来了。云爱不是多愁善感的女孩,倒没有伤春的情怀。况乎生活在大城里,春也就是那个调调,既无花团锦簇的春景,又缺少诗意的春情,排成队的行树容颜憔悴,连个性都被修剪掉了。前些时,杜鹃倒是喧闹过一阵子,一场雨后,也就落英遍地,成了春色的残迹。
校园里的季节更为暧昧,大王椰绿得焦焦的,传说会说话的杜鹃只是年轻人的乱梦衍成的传说,多少带些自怜和自嘲生活如果炽热而多采,何必寄望于杜鹃真能解语呢?
没进大学时,云爱有过喷泉般的热梦。那时候,她被大书包、鸭屁股般的发型、不可计数的训导条规、近视的威胁、联考的压力整得头昏脑胀,只有越过恼人的现实,像栽花般的栽种她美丽的梦。
进入这所著名的大学,将近一年了,总觉空荡荡里有些混乱,有一种初次飞翔的雏鸟般的惊怯。当然,和高中生活比较,天宽地阔得多。她留了清汤挂面式的长发,走起路来,一路牵得起一点春风了,那比脑后一块青,当然要惬意得多;她可以有权选择衣服的颜色,而且理直气壮蝴蝶都有权选择颜色呀,何况十九岁是少女生命里最绚灿的春天。
配合衣着和发型的改变,满眼五色缤纷的海报,各种看来热烈无比的社团活动的消息,气氛特殊的迎新会,都狠狠的使她着迷过一阵子,意义如何,且不必多去追究,至少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就够人迷醉的了。
后来听到高中时代的密友,如今又是同系同学的柯凤珍说,这种迷醉叫新生狂,仿佛是一种在整体教育环境感染下,自然产生的共同感觉,就像传染性的精神疾病,最多维持一学年,然后便会像眠过的蚕,朝更成熟的领域跨进了。
柯凤珍是个打算以奖学金填满大学生活的女孩子,理性强,善思考,特别着重人生实务,在某些思考性的人生问题上,谈论起来,习惯的推动金丝边的眼镜,凛凛然有些先知的味道。在这方面,云爱常被她的说服力催眠,但过后总有些感觉,觉得凤珍生活得太刻板,差一份潇洒,欠一份梦幻,浑身上下,找不出诗味来。她崇敬对方的理论,却不惯苟同她那种生活模式。比较起来,她和她的另一个密友,如今也是同系同学谈小雯,倒是更为投契。
说是新生狂也罢,人总很难抗拒新鲜事物的吸引的,她和谈小雯参加了好几个游乐的社团和谈论的社团,着实疯了一阵子。生日派对啦,土风舞会啦,合唱团啦,郊游野营啦,国乐社的定期演练啦,满天星子闪烁的夜晚,浪漫的音乐,旋律优美的歌声,充满欢笑的舞蹈,配合那种年纪,不能说不是美的。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轮覆过来,还不到一学期,云爱对这种软性的抒情式的生活,就感到厌倦了。如果光是为了吃点儿,玩点儿,何必要拼得两眼发黑,挤进大学来呢?念头只要不着力的轻轻一转,新生狂那股热劲儿,立刻就冷却了,凝固了。
真的,小雯,我们是放了缰的野马,乐上瘾啦,她对谈小雯认真的说:这学期,上课应卯,心不在焉,成天想着玩,我们该收收心,顾顾功课啦!
你是被柯凤珍说服了?云爱,谈小雯说:她天生是出国型的博士命,咱们想学样也学不上,何必太认真呢,不玩白不玩,卖酸装乖,我不干。
云爱懂得人各有志,不可相强,也就不愿再说了。倒是小雯觉得这样顶撞云爱,有些不好意思,想了一想,又接着说:
其实,妳也顾虑得对,成天去疯去野,有时我也觉得腻得慌,有些更有意义的社团,我们应该参加。我觉得,读大学不光是死啃书本,而是要读生命,读感觉,妳說对不对呢?
对啊!云爱温和的笑笑:我也是这么想,但我自己总觉得心很散,功课太荒疏了!
云爱想了又想,她为什么会陷在那些游乐的、闹剧式的活动里这么久?柯凤珍指称那些活动,都只是一种烟幕,在每个人沉潜的意识里,大多具有求爱和择偶的欲望,不过是苗家跳月的花样翻新罢了!柯凤珍固执的认为那很使她觉得无聊,更有点恶心。云爱自承她的看法,要比柯凤珍宽和得多。不论男孩和女孩,到踏进大学门后,身心都趋向成熟了,经由正常的社交活动,自然的增进情感,即使谈谈恋爱,谈论婚姻,也算不得是罪过。柯凤珍的观念,也未免古怪了一点。
但无聊之感,本身也是有的,社团是高年级表现的天下,清汤挂面型的新生,不过是些龙套,多你不多,少你不少,被冷落的味道,毕竟不太好受,抗拒和厌倦的意识,自然也跟着来了。
有些道理不必说给别人听,时代啦,责任啦,人生基本课题啦,凡是成为口号的东西,都不一定能和眼前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至少,说得平实一点,在学校生活里,多读些书,多吸取知识充实自己总不错的。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高二时,国文老师常摇晃着大白头,秋风里的芦花似的,朗吟着这个,云爱真的感动过。但也许是暮春的缘故,人很困倦慵懒,有时听课,觉得眼皮很沉重,教授的声音越来越远,讲台上的那张脸,也像在水波上晃动起来。远山是蜷卧着打瞌睡的猫。阳光亮得使人想买一架莱卡。彩色照片的冲洗费愈来愈便宜了。甚至为一只迷在教室的蜜蜂乱撞玻璃去拉开窗子。蜜蜂可以飞出去,用翅膀承载阳光,而同学们必得坐等着查堂点名什么的,教授变成一只飞不动的蜜蜂了。
勉强一点罢,云爱,她总这样劝慰自己,教授们不都是天才的演说家,如果把课程密度增浓到某种程度,钟点费岂不太便宜了,她并不希望那样,因为精采的往往是举例掺水的部分,满室哄笑给人的振奋,远超过克劳酸华蒙D的效果。
不过,既无内容,复缺创意,照本宣科读讲义,连水都不会掺的教授,偏吃上这行饭,既误了旁人又害苦自己,那就太伤感情了。云爱发誓这学期要把余下的通史课全翘掉,她不忍看戴了假牙的老教授在捧着数十年不变的老笔记呻吟时,把假牙掉在讲台上的惨状,使她笑得有要哭出来的感觉。
能怪谁呢?真实和梦想之间,总有一大段差距的,等自己从切身体悟中明白这一点,当年的热梦倒成为自掘的陷阱了。假牙事件发生后,有个男同学拟了一副联语,写在黑板上,上联是:
传道,授业,解惑,为师为患。
下联是:
资格,权威,饭碗,难舍难丢!
翘这样的课该算是慈悲为怀罢?生活就是影剧,也该有些适合的剪裁呀!从课堂走出来,夕阳的余晖洒在校园里,云爱挟著书,走在不开花的凤凰树下,透过细碎叶簇的阳光染在她淡色的衣裙上,仿佛替她披上了一身光灿的羽毛,她不是一只真正的青春鸟,是鸟,她早就飞到天顶的云外去了。如今她走着,夕阳很绚烂,但在她眼里,却也有些凄清。
也许埋头在图书馆不很明亮的灯色里,能找到一些答案罢?
云爱的班级,是个热门的大系,放榜时,名单上塞了一百多人。据说贴红纸;放鞭炮,为子弟名登金榜大宴宾客的人家不在少数。一个学期过去了,云爱认识班里的同学,最多十之二三,经常有些看来陌生的面孔,问起来才知道是一个班上的,云爱很感慨的对谈小雯说:
尽管没有龙王庙的大水,全班的同学,我怕到毕业都认识不完啦!
也许旁人也有同样的感觉罢?同车同船都是缘,何况同窗四年,如果真的到毕业,彼此都叫不出名字,那也太说不过去了!所以有人提出增强班际活动,组织新的社团,要以全力推展班际活动作为团结的基础,进而参与校际活动,把年轻人的光和热都发射出来!
这时候,云爱有些意兴阑珊,班际活动和一般社团活动,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仍是谈呀、玩呀、跳呀、唱呀那一套,不过人头不同,换成班上的同学而已。这种活动勉强把大家拢在一起,群性是有了,个性却逐渐减少,同学们像养在玻璃缸里的缺氧的鱼群,彼此将自己的梦呓吐成摇摆上升的泡沫,而心底的寂寞却渊如大海。
想钻进书堆钻不进去,想凑热闹又落得一身疲倦,云爱回到家里,对著书桌上的台灯,常常用发呆打发夜晚。成长和蜕变,是一种撕裂性的痛苦,作为一个大学生,该有若干的抱负和理想,有许许多多有意义的事情要做才对,但云爱不知道在这种环境里她能做什么?忽然她想抛开这些恼人的问题,找些自己的事做。
一天,在图书馆里她遇上教通史课的老教授,云爱在课堂曾经讨厌过他,老教授正在她前面,费力的爬楼梯。他的头发已经很稀疏花白了,肩臂有些僵硬,微微佝偻着,他每登一级楼梯,就得用拐杖用力的触地,支持他已经不很灵便的身体。云爱不愿意超过前辈走到前面去,便在他身后跟着。两人相隔三四级阶梯,她仍能清晰的听出他急促的喘息声。
在这一刻,一向顽存在她意识里的憎厌完全化解了,她的心满是温柔的关爱,无论如何,他把一生都耗在教育工作上是事实,如果不把他看成一个教授,把他看成一个老祖父,自己不该爱他吗?
在上楼梯的最后几级,老教授停住了,云爱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冲动,赶着跨上去,轻轻的扶着他。
老教授望着她,他熟悉她的面孔,却叫不出她的名来,他笑笑,低哑的说:
妳是?
我是经一,选您的通史课的,我叫云爱。
啊!老教授吁了一口气:我老了,眼很拙,常常认不出同学来。
我常翘课,云爱微红着脸,鼓起很大的勇气说。
老教授没说什么,轻轻拍云爱的肩膀,显示出他的关爱,然后说了一句谢谢妳,他们就分开了。
云爱从图书馆回家后,又在灯下发起呆来,她想起这一年大学生活很混乱冗杂的原因,主要是对事物的体认不完全,价值判断总是游离不定,社会观,学术观,人生观,甚至恋爱观都很朦胧。整个的人,常随着情绪的起伏,表现出多变的喜怒和爱憎,拿通史教授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种彷徨和挣扎,同样也在谈小雯身上显示出来,谈小雯经常打电话来给云爱,有时兴高采烈,谈起很多传闻的趣事,笑得连电话线都发抖;有时闹起情绪来,埋怨这,抱怨那,一讲能讲半个钟头还不肯放下电话筒。
有时她约云爱去逛街,坐咖啡店,她的话题逐渐的转到学校里的某些男生的头上,她烫了头发,也讲究起衣着和化妆了。
怎么样?小雯,云爱说:妳谈上恋爱啦?
谈恋爱?谈小雯说:跟谁谈恋爱啊?我才不愿意早早被人敲定呢!我只是想跟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傻蛋们周旋周旋罢了,带点儿仿佛是初恋的情绪,实际上决不当真,这要比那些团体喧闹有味道得多!
云爱想想,和男孩子们正常的交往,也并不算坏。在一次生日舞会时,数学系有个大眼睛的男孩,曾经邀她跳过舞,并且痴痴迷迷的注视她,云爱开玩笑的送给他的一个外号,叫猫头鹰。第一面的印象很深刻,她坐在长窗边,拿他的眼镜当着镜子。
那男孩挨着她坐,眼睛闪着光。
妳认不认识我?我就是未央歌里的小童呢!
她快乐的大笑起来,觉得他大言不惭得很可爱。事实上,云爱愈来愈喜欢和男孩子们交往和聊天的,他们谈起话来,话题比较广阔。有时候,他们表现的生命力和责任感,也满迷人的;有些话,是她在周围手帕交之中永远也无法听到的。
她没有跟小雯提起这些,即使在最要好的朋友面前,也应该有些小小的、全属私人的秘密的,可不是?
但谈小雯却把云爱当成倾诉的对象;她说她选择朋友,和选择对象虽然性质不同,但也具有若干很微妙的连锁关系,难道对象不是从认识的朋友里面,精挑细拣出来的吗?
云爱也知道,谈小雯和男孩交往,抱的是三不同主义,那就是不同班,不同系,不同年级。谈小雯认为同班同系的男同学,天天在一起要过四年,彼此太熟悉了没什么神秘感,如果真的恋爱,也像喝薄荷酒,甜甜淡淡的沾那么一点酒味,不会醉人。她喜欢强烈的,旋风式的,能把人吹到天上云上去的那种可生可死的爱情。
学校里的几个高年级的领导人物,像文光社的曾唯明,办刊物的总编辑张光治他们,都是谈小雯很想攀上的。但那些人使人在感觉上多少有些趾高气扬的味道,他们眼里会不会有这些大一的、土土的黄毛丫头还大有问题,她怕谈小雯早晚会失望的。她把这意思和谈小雯讲过,而对方却另有她的看法。
什么是土土的?什么是洋洋的?谈小雯说:改改发型,穿穿耳洞,买套威格一穿,照样喷出火来。再说,男孩子那种趾高气扬的味道,还不是众多女孩众星捧月宠出来的?男孩是鱼,没有不吃饵的,钓鱼也有钓鱼的方法,妳为何不试试呢?
云爱不想试,只觉心里很乱,又空又闷。
期中考后,谈小雯硬扯着她去穿了耳洞,烫了头发,并且对她发表议论说:下学期升上大二了,人要像蚕一样,眠过一眠,就要长大一点,早晚总要改变的。
不论谈小雯怎样替她壮胆打气,云爱回家关上房门,一个人照了一晚上的镜子,总觉镜子里的影像怪怪的,越看越不像自己。第二天,她打电话,托谈小雯替她请了一天的假,但躲也只能躲一天,第三天来到学校,云爱总觉得走在街上,一街的人都在看她;搭上公车,全车的人都在看她;学校里的同学,也都瞄着她的耳洞和卷曲的头发;使她总是低着头,连肩膀都有些不自然的僵硬,使她恨谈小雯拖她下水,更恨自己耳根太软,即使人生真的像蚕罢,也不能在初眠之后就急于作茧啊!
说也奇怪,云爱发型改变后不久,数学系的那只猫头鹰居然把她当成小鸟啦,他诚心来约会云爱,云爱故意不拒绝,看看猫头鹰究竟想做什么。
猫头鹰请她进冰店,用大眼睛瞄着她,意味深长的冲着她笑说:
嗳,李云爱,妳是否想过,一个女孩子急于改变她自己的外观,具有什么样的精神意义?
云爱也看着对方,但看不见他的眼,只见到镜片上的闪光,上面有两只怪怪的自己,像两只蝴蝶。
我又不是学心理学的,她故意反问说:依你看,有什么精神意义呢?
我看,嗯,他把眼镜取下来了:我看她该是内心太寂寞,急于交异性朋友了。人说:女为悦己者容,要不然,花那么多的精神,不是白费了吗?
这像伙单刀直入,说到云爱的心底去了。云爱承认,有些事不经别人提醒,自己实在很难体察出来,但若就这样点头承认,让对方露出洋洋自得的面孔,未免太给他面子了。这样一转念,便轻哼一声说:
看你这样自信和神气劲儿,有点铁口和半仙的味道可以到中华路挂块招牌混饭吃了!
我宁愿业余玩儿票,猫头鹰说:只要妳一个人承认就好!
猫头鹰在男孩里特出吗?也并不特出。说他是谈小雯所形容的那种自以为聪明的傻蛋吗?也不至于差劲到那种程度,也许他只是云爱精神荒原上的小花小草,多少可以点缀点缀缺乏水分的感情生活,离开所谓的恋爱,还有十万八千里,如果说普通的友谊,那还差不多。
不过,她不能单纯的依靠这点儿友谊去润饰自己,在谈小雯热心的拉扯之下,她更深一层的投入了校际生活。云爱和谈小雯从初中到大学,相处的历史很久,她对这位好友也了解得很深。小雯人很活泼,聪明,心地也好,只是有点爱慕虚荣,不太甘守寂寞,常爱对男孩子们耍点小技巧,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她并不曾用低估的眼光看扁别人,甭说是小雯,学校里大多数同学都有同样的毛病。他们把书本的知识和真实的人生学问混淆了,误认为只要多读几本书,肚子里就装进了世界。俗语说:满瓶不响,半瓶晃荡。这些高级的年轻知识份子,大多是半瓶醋,或是一枚拥有一点工具知识的螺丝钉其中当然包括她自己在内。云爱也明白,连对谈小雯都没有透露过。
谈小雯顺着她的心意发展,终于和学校的风头人物曾唯明和张光治他们攀上了。文光社那时正全力拓展组织,扩大吸收新的会员,曾唯明以社长的身份,用礼贤下士的态度,到处奔走。有一天,他等在教室门口,找上了谈小雯和云爱。
对不起,鄙人很冒昧,诚心邀请两位文化人,参加本社的编辑群。他又打千,又作揖,云爱嗅得出他光亮的头发上一股宾士发霜的味道。随着,他掏出两张很大的名片,递到她们的手上。其实这完全是画蛇添足,他们早已见过面,互相认识了,也许曾唯明是想用名片上那一堆头衔唬小女孩罢?云爱却是不吃这一套的。
尽管如此,云爱还是抱着玩票的念头,参加了文光社,对别人却说这是她理想的执着,因为这是校园里最流行的一句话,用它可以省却解释的麻烦。她参加文光社,实际上是想在多面生活里去体验,尽量把生活拓宽一点,免得被猫头鹰单独的纠缠住,去赴他那种有些被动感觉的约会。
文光社说是文艺性的社团,其实参加的成员,没有几个是认真搞创作的。他们的聚会,多采讨论型式,讨论社会,讨论生活,讨论文化,讨论各自抱有的五花八门的理想。曾唯明在这些讨论中,总以社长的身份,以无形的精神领导者自居,往往两小时的聚会,他的开场白先占四十分钟,一个结论又占了四十分钟,这样还意犹未足,常常站起来说:本人退出主席的地位发言。
什么鬼讨论会?有人公开表示不满说:这该叫曾唯明时间才名副其实。
曾唯明是我们校园诗人,凡是诗人,时间观念可能都比较淡薄些,有人嘲谑说:他认为他的精神空间容纳我们这些社员还有什么问题? !
云爱没说过什么,透过文光社的活动,她实在学到不少,也悟到不少。曾唯明的手腕好,经验足,有人形容他是专搞社团活动的老千,到底老千到什么一种程度,云爱还不敢骤下定论,至少,她看得出曾唯明调子唱得高,内心对人却缺乏诚恳,他的慷慨陈词,只是他的个人表演,他惯会用技术性的方法,指使这个,差遣那个,仿佛把全体社员当成一盘棋子,任他捏着走。他找上谈小雯和自己,也不过是替他旗下增加两个喽啰罢了。这种人浑身上下毫无诗味,偏偏要打着诗人的旗号,使云爱困惑的眨了很多次眼,还是想不透什么原因。
而谈小雯却被曾唯明盖住了,曾唯明喊创新,她就觉得创新是好的;曾唯明谈虚无,她就觉得虚无有道理。在这种情形下,云爱只有悄悄的抽身隐退一途了。
学期快结束时,校园里却起了精采的高潮,因为由张光治为首的一群,看不惯曾唯明一手垄断文光社的作风,一心要改革文光社,他说:
如果曾唯明仍然不放手,干脆让文光社瓦解,精神上还干净一点。
一向唯我独尊惯了的曾唯明,忍不下这口气,到处打躬作揖,采取低姿态笼络群众,挂上悲剧脸谱争取同情,更到处用悄悄话放空气,说张光治是学校方面安排过来的卒子,文光社的活动,张光治总是扯他后腿!
张光治外号硬派小生,果断、敏锐,不但能言善辩,而且对于他要打击的对手穷打猛追,毫不留情。曾唯明在系刊上发表的新诗,张光治公开的批评说:他写的什么鬼新诗?还不如庙签呢!
曾唯明脸都气绿了,可也不甘屈居下风,他反唇相讥说:
张光治那小子,身兼好几个家教,翘课翘到天外去了!根本是职业学生!
明争和暗斗继续着:曾唯明指张光治是内容贫乏的白板,张光治就反指曾唯明乱追小妞,两人一面攻讦,一面用尽各种挖角的方法拉人帮腔。闹到最后,旁人不愿意卷入这种无聊的是非,一个个都拔开腿开溜了,只剩下一个光杆社长和一个孤掌难鸣的总编辑。
云爱在图书馆里,遇上啃书的柯凤珍,对她说起文光社的这场风波,柯凤珍推推金丝边眼镜,淡淡的说:
这种狗咬狗的事,我早就料到了,在这样好的环境里,我只想多读书,多充实自己,我们所学的一点工具知识,是要服务社会的,至于民族啦,文化啦,那些人生的大题目,我们只有虚心探求,哪配洋洋自得的滥发宏论?那些男孩子,傲气十足,半点也不虚心,我看到了就反胃,妳不提也就罢了!
云爱想想,柯凤珍的话实在有道理,张光治和曾唯明的言论有什么可取?有什么深度呢?他们总抱着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以一种不成熟的反抗心理,指责社会现况,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来,其实,社会生活,文化根蒂,他们根本缺乏透视,说句不中听的话,这些以老大哥自居的学长们,根本还没长大。记得有一回张光治发言议论,主张把贪官污吏全丢到海里去喂鱼,使很多人为他鼓掌;曾唯明主张俭以养廉,但他花起他家老头的钱就像流水似的。
浪花涌过去了,心里留着沙沙的泡沫破裂声,成长和蜕变,真的是够痛苦的。人该寂寞一点,忍受着、等着真正的成长罢?
她不再到文光社去,曾唯明却找到了她。他的模样有些憔悴,垂头丧气的对她诉苦说:
嗨,妳们女孩子,真幸福!每天躲在花丛里数星星,哪里知道我们搞社团,拼得头破血流?
算了罢,社长大人,云爱说:我现在只要一点安静。
我真实也拼累了,要些安静了。曾唯明说:我跟张光治两个,决定握手言和,我当社长,他当副社长,朝后决不再争执啦!
后来云爱听谈小雯说,曾唯明和张光治两个,真的和解了,决定重建文光社,两人绞尽脑汁,贴出号召社员回队的大海报,把各种好听的字眼全用上去了。
云爱有些兴味索然,偏偏这时候肥头大耳的猫头鹰又来纠缠,云爱倒愿意和猫头鹰聊聊说说,破破心里的闷气,但对方斩钉截铁的认为男女之间没有友谊的存在,以一副不折不扣的王尔德信徒的姿态,逼着云爱摊牌。
我们吹了!云爱简单的说。
日子在表面上过得像满多采的,但云爱的心里,又白又冷。校庆那段日子,文光社筹办了一个大型的书展,曾唯明和张光治两个,硬拉云爱去帮忙,谈小雯做书展小姐,一口气做了三套亮相的新洋装,云爱老实,就担任管理账目的工作。
书展办下来,大赚了一笔,云爱把账款交出去,曾唯明和张光治两个家伙,竟然把谈小雯带出去,公款私用开庆功宴去了。
连吃带玩,花掉了一千七百块,由于要对全体社员公布账目,他们一时无法弥补,竟然认定云爱好说话,请云爱在账册上记上一千块钱筹办交际费,三百块钱车费,四百块钱呆账。
这真是我第一次碰上的新鲜事? !云爱张开嘴,呆了半晌说:我不愿淌你们的浑水,你自己记罢。
何必呢?小姐!张光治说:妳是没吃到,受了委屈啦,我私人补请妳一次就是了!
去你的!云爱想不到自己竟会这样大发脾气:你凭什么要把贪官污吏丢下海喂鱼?没出学校门呢,新贪墨记就开演了,账册拿去!
她用力把账册飞掷到张光治的白脸上,骑上脚踏车回家了!
夜晚,云爱激愤逐渐平复了,躺在床上,双手交叉在脑后,看着窗外的月亮。她记起路加福音第六章有这样的话:看见别人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像张光治和曾唯明他们,实在该读读这节经句的。
如乳的月光倾泻下来,那么柔,那么美,真是太奢侈了!使云爱睡不着。云爱觉得月亮像一个小女孩带笑的嘴角,弯弯的翘着;然而,农夫会觉得它像割稻用的镰钩罢?农妇呢?一定会觉得像她那柄牙梳了!
白天遭遇的不快,真该忘记了。云爱想,这还早着呢,等到四年大学生活过了,每个人编织的梦,也该是截然不同了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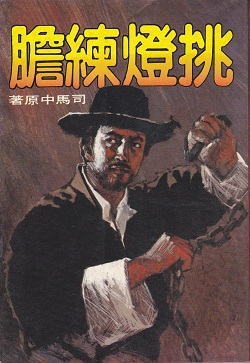
挑灯练胆
司馬中原
小说园地
类别- 2023-02-05发表
-
107955
已完结
© www.iabbook.com
按 “键盘左键←” 返回上一章 按 “键盘右键→” 进入下一章 按 “空格键” 向下滚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