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杰夫.温斯顿死前,正在和妻子通电话。
妻子正说到我们需要,但杰夫再也听不见他们需要什么,似乎有某个重物击中他的胸口,让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电话筒从他手中滑落,敲碎了书桌上的玻璃纸镇。
一周前,她才说过类似的话,她说,杰夫,你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吗?接着是一阵停顿,明显的暂停,但不像这次要命的停顿无止尽、无可更改。当时他正坐在餐桌前,琳达总爱叫这里早餐角,尽管一点也称不上是个独立空间,不过是张小小的耐热树脂桌配上两把椅子,笨拙地摆在冰箱左边和干衣机前的角落里。说这话时,琳达正在流理台上切洋葱,也许是眼角的泪水让她的问题比原先预期多了些分量,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好好想想。
杰夫,你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吗?
原本他该一边读着休.塞迪在《时代》杂志上讨论总统大选的专栏,一边用漫不经心、毫不关切的语气回她,我们需要什么,亲爱的?但杰夫这天并没有心不在焉,也没对塞迪的闲扯蛋骂句该死。事实上,他很久很久以来都没如此专心、集中注意力过。因此他有好些片刻没说半句话,只是盯着琳达眼角的假泪,努力想着他们他与她到底需要些什么?
他们需要出去透透气,调剂生活,需要搭飞机到气候暖和、碧绿苍翠的小岛,说不定是牙买加,或是巴贝多。自从五年前那趟计画许久结果却有点失望的欧洲之旅后,他们就没再好好渡过假了。杰夫没算上每年的佛罗里达之旅,到奥兰多探望父母、到博卡拉顿探望琳达的家人不过是拜访一段不断模糊远去的过去,没别的了。不,他们需要的是一礼拜或一个月的时间,到颓废堕落的异国小岛上尽情逍遥:在绵延无尽的无人沙滩上做爱,晚上听着如火红花朵香气飘荡在空中的雷鬼音乐。
一幢好房子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也许是在蒙克莱登山路上的豪宅,他们多少次在礼拜天开车驶过时对此渴望不已。或是位于白原市的房子,里奇威大道上一栋十二个房间的都铎式建筑,靠近高尔夫球场。不是他想打球,不过相较于位在通往布鲁克林︱皇后快速道路边坡或是拉瓜地机场降落航线上的房子,那一片片叫枫野、威却斯持丘的慵懒绿地才是较宜人的居住环境。
他们也需要一个孩子,琳达或许比他还急。在杰夫想像中,他们从未出世的孩子总是八岁大,跳过了需索无度的婴儿期,但又还不到恼人的青春期。一个乖小孩,不过分漂亮或老成。是男孩女孩都不重要,只要是他们两人的孩子,他会问逗趣的问题,会坐得靠电视机太近,举止中会时而闪现成形中的独特个性。
但他们不会有孩子。从一九七五年琳达子宫外孕开始,他们知道这件事不可能已经好几年了。他们也买不起蒙克莱或白原市的房子。杰夫的职位是纽约WFYI全新闻广播频道的新闻总监,实际上的名声与收入不如听起来响亮丰厚。也许他该跳槽到电视台去,不过以四十三岁的年纪来说是不太可能了。
我们需要,需要谈谈,他想。他们需要直视对方的眼睛,简单地说句:我们走不下去了。浪漫、激情、美好的计画,没有一样行得通。全都变得平淡无味,而且也怪不了谁。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他们当然没有谈谈。这正是他们最大的失败,他们很少谈及内心深处的需求,从不曾触及始终存在两人之间撕扯般的残缺感。
琳达用手背拭去洋葱引起的无意义泪水。你听到我说的话吗,杰夫?
是,我听到了。
我们需要的是,她说,一边看着他的方向,但视线不是落在他身上,一个新浴帘。
她在他步向死亡前的那通电话里,十有八九要表达的也仅是这种层次的需求。一打蛋,或许话就这样结束,也可能是一盒咖啡滤纸。
但他为什么想这些?他纳闷。他正在死去,看在老天分上,难道他最后不该想点更深入、更有哲理的事吗?或是将他的毕生高潮来个快速重播,四十三年的精华剪辑。人溺死时,不都曾走过这一遭?感觉就像溺水,他在思考时,仿佛被拉长的时间一秒秒过去:那骇人的压力、想吸口气的绝望挣扎,使他浑身湿透的湿热水气,就像从他前额淌下、刺痛双眼的咸味汗水。
他正在溺水,正在死去。不,吃屎去,不,这不是个真实的字眼,只有花、宠物或其他人才用得上这字眼。只有老人、病人、不幸的人才会死。
他的脸落到书桌上,右颊平抵着琳达打电话来时他正要开始研读的档案夹。在他睁开的一只眼睛前,纸镇上裂开的缺口像个巨大的洞穴,世界自身的裂痕,反映他内在极度痛楚的一口破镜。透过破碎的玻璃,他看到书架上方数位时钟上鲜明的红色数字:
1:06 PM OCT 1888
接下来再没有什么需要避免去想了,思考过程已然终止。
杰夫无法呼吸。
他当然没办法,他已经死了。
但是如果他已经死了,为什么他能意识到自己无法呼吸?或意识到任何事?就死了这件事来说,这不该发生。
他从卷成一团的毯子上转开头,开始呼吸。闷湿的空气中充满了从他身上散发出的汗味。
所以他没死。不知何故,意识到这件事并没有让他太兴奋,就像之前的死亡假设也没能吓着他一样。
也许他曾窃喜来到生命的终点。现在一切只能照旧下去:满怀不平地承受着野心与希望落空带来的折磨,而他再也记不得那段失败的婚姻究竟是原因,还是结果。
他把脸上的毯子推到一旁,踢了踢起皱的床单。黑暗房间里正播放着音乐,乐声细不可闻。一首老歌,曲名是<嘟啦啦>,来自菲尔.史贝克特捧出来的女子乐团。
杰夫摸索着想找到电灯开关,在黑暗中完全了迷失方向。他要不是正躺在医院的床上等着从刚才办公室里发生的事件中复原,要不就是在家里,刚从比平常还恐怖的恶梦里醒来。他的手摸到了床头灯,开了灯。他发现自己正在一个狭小脏乱的房间里,衣物和书散落一地,或胡乱堆在两个相邻的书桌上、椅子上。不是医院也不是他和琳达的卧房,不知为何,却有股熟悉感。
面带微笑的裸体女郎正从贴在墙上的大照片上回望他,是《花花公子》的折页海报,属于早期风格。肤色浅黑的大胸脯女郎故做正经地以腹部撑地,躺在一艘船后甲板的气垫上,栏杆上绑着她的红白圆点比基尼。她头上戴了顶漂亮时髦的圆形水手帽,黑头发仔细做过整理和造型,使得她与年轻时的贾姬出奇相像。
他看到其他墙面也都装饰着过时的青少年时代风格:斗牛海报、大幅积架XK︱E黑色跑车照片、戴夫.布鲁贝克的旧唱片封面。一张书桌上方有个红白蓝三色条幅,上面用星条图案的字体写着操!共产主义。杰夫看见那标语时笑了,他记得自己也曾从保罗.克雷斯纳轰动一时的小众杂志《现实主义者》上订购了一条,就跟这个一样,那时他还在读大学,那时
他突然直挺挺地坐起身,耳中响起突突的脉搏声。
他还记得近门那张书桌上的老旧鹅颈灯,每当移动它时总是会从底部松脱。也还记得马汀床边地毯上有块很大的血红污渍没错,就在那里杰夫有次偷渡茱蒂.高登上楼,茱蒂跟着漂流者的音乐绕着房间起舞,打翻了一瓶义大利红酒留下的。
刚醒来的朦胧困惑已经消失,他现在彻底糊涂了。他匆匆掀开身上的被子下床,摇摇晃晃地走到一张书桌前,他的书桌。扫视了堆在桌上的书:《文化模式》、《萨摩亚人的长成》、《统计母体》,都是些社会学入门读物。是丹福德还是山朋博士的课?在校园遥远一端充满霉味的大讲堂里,早上八点的课,他总是上完课才吃早餐。他拿起班乃迪克的书翻阅,有几个地方已经密密麻麻地画过了重点,书页边还有他手写的笔记。
WQXI的本周热门音乐来自水晶乐团!接下来是卡罗和宝拉点给玛利叶塔的鲍比的歌。这些漂亮女孩们想告诉鲍比,她们的看法就跟雪纺纱乐团的女孩一样,觉得他真是棒极了
杰夫关掉收音机,抹去前额冒出的一层汗水。他有点不自在地注意到自己已完全勃起了。还没想到性方面的事就这么硬,上次这样子是多久以前了?
好了,该好好理出个头绪来。肯定有人精心设计要捉弄他,但他不知道有谁玩整人游戏。就算真的有,又有谁愿意如此大费周章?他在上头做过笔记的书好多年前就丢了,没人有办法复制得如此维妙维肖。
书桌上放着一本影印的《新闻周刊》,封面故事是西德总理康拉德.艾德诺的下台,期号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号。杰夫一直盯着那数字,希望能为一切想出个合理解释。
全都说不通。
房间门猛地弹开,卧室内的门把砰地撞上了书柜。就像往常一样。
嘿!你还在搞什么鬼?还有十五分钟就十一点了。我以为你十点要考美国文学。
马汀站在门口,︱手拿了可乐一手拿了堆教科书。马汀.贝利,杰夫大一时的室友,整个大学时代直到毕业后几年一直是他的密友。
马汀一九八一年自杀了,在离婚及接连的破产之后。
所以你打算怎样?马汀问,拿个不及格?
杰夫看着他过世已久的老友,惊讶得说不出话来:马汀那发线还没后退的浓密黑发、光滑的脸庞,尤其是那对洋溢着青春光彩、不曾见识过苦痛的眼睛。
嘿!怎么回事?杰夫,你没事吧?
我觉得不太舒服。
马汀笑着把书本扔到床上。跟我说怎么回事。我现在知道我爹为什么警告我别碰苏格兰威士忌混波本酒了。喂,你昨夜在曼纽尔酒馆碰上哪个甜妞儿吧?茱蒂如果在,肯定会杀了你。那女孩叫什么?
呃
少来了,你没醉成那样。你会打电话给那女孩吧?
杰夫在极度惊慌中转过身。他有太多事想告诉马汀,但比起现在的疯狂状况,没有一件事能让人容易理解。
出了什么事啦,老兄?你看起来他妈的糟透了。
我,呃,我得出去一下。呼吸点新鲜空气。
马汀一脸困惑地对他皱了皱眉头。对,我想你需要。
杰夫抓起随便扔在书桌前椅子上的一条卡其裤,然后打开床旁边的衣柜,找到一件薄棉T恤和灯芯绒夹克。
到医务室去。马汀说。跟他们说你感冒了,说不定盖瑞会让你补考。
我会。杰夫匆匆穿好衣服,套了双马皮便鞋,他的换气过度症快发作了,他强迫自己得慢点呼吸。
别忘了今晚要去看希区考克的《鸟》,茱蒂跟宝拉会在杜利餐馆跟我们碰面。我们要先吃点东西。
没问题,晚点见。杰夫踏进走廊,关上身后的房门。他往下冲过三道楼梯,当经过的某个年轻人叫住他时,他敷衍地喊了声又!回去。
宿舍大厅跟他记忆中一样:右边是视听室,现在空空荡荡的,但每逢运动赛事或太空梭发射时就挤满了人。几个女孩聚成一团吱吱喳喳,正等着男朋友从楼上的禁地下来。布告栏上贴着学生的告示,卖车、卖书、分租公寓或征求到马康、沙凡纳或佛罗里达的便车,对面有台可乐贩卖机。
外头的山茱萸木正值盛开季节,将校园妆点成烂漫旖旎的粉白世界,显映着宏伟希腊罗马式建筑的白色大理石。这里无疑是埃墨里大学,美国南方为创造出古典长春藤风格大学所精心打造的校园,好让地方上的人也能以拥有自己的长春藤大学自豪。这类建筑的永恒特质使人失去判断力,当他缓缓穿过四方形建筑,路经图书馆、法律大楼,杰夫忽然领悟,在这里很容易把一九八八年当成一九六三年。校园广阔绿地上,学生们正漫步闲晃,就算是从他们的衣着和发型也找不出蛛丝马迹。除了活像浩劫余生的庞克造型外,八○年代年轻人流行的穿着根本和他大学早年时期没多大差别。
老天。他想起曾经在这校圔里度过的时光,从这里诞生却从未实现的梦想。那里有座小桥通往神学院。他和茱蒂.高登曾有多少次在这里消磨时光?再过去是心理学馆,大三那年他几乎每天都和盖儿.班森约在那边见面一起去吃午餐,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女人拥有真正亲密的柏拉图式友谊。为什么他没从和盖儿的友情中学到更多呢?他透过许多不同途径,最后漂流到一个遥远之境,远离诞生在这宽心平静的绿草地上、高贵建筑物里的计画与抱负,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在到达主校园的入口前,杰夫已经跑了约一哩的路,他原本预期会气喘吁吁,却没有。他站在格兰纪念教堂下方的矮丘上,下望得卡图北路和埃墨里村,那供应校园所需的小小商业区。成排的服饰店与书店看来似曾相识,其中一家哈顿药局更是勾起他一波波的回忆:他可以在脑海中看见画面,杂志架、长排的白色苏打喷泉、附有个人点唱机的红色皮革雅座。他还能从某个雅座的桌子对面看见茱蒂.高登青春洋溢的脸庞,闻到她干净金发散发的味道。
他摇摇头,重新专注于眼前的风景。一样,还是无法分辨现在是西元几年。自从一九八三年美联社举办恐怖主义与媒体研讨会后,他就再也没到过亚特兰大了,而自从多久了老天,也许从他毕业一、两年后,他就没再回去过埃墨里大学了。他完全不知道那里的店家是否还是老样子,或许已经被新盖的大楼,说不定是个购物中心取代了。
车子倒可以提供线索。他一注意到这点,就发现下面的街上看不到一辆日产或丰田。全都是老车,大多是大又耗油、在底特律生产的美国车。他看见的老车可不只是六○年代早期的车款,呼啸而过的庞然巨兽有一堆都是五○年代的车,不过当然了,不管是一九六三年还是一九八八年,路上车龄六年、八年的车子都一样多。
他还是没法下定论,甚至怀疑在寝室和马汀的短暂相遇是否只是个不寻常的逼真梦境,一个他醒来前做的梦。他现在十分清醒,而且身在亚特兰大,这是事实,毫无疑问。也许他想借酒浇愁,想忘却他沉闷混乱的生活,他喝醉了,然后在一时冲动下,出于乡愁便搭上了午夜班机来到这里。满街的过时车款只是个巧合。任何时候都可能会有人开着他已司空见惯的小巧日本车从眼前经过。
有个简单方法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大步走下山,朝得卡图路上的计程车招呼站走去,三辆蓝白相间的计程车在排队,他搭上最前面那辆。驾驶是个年轻人,也许是个研究生。
上哪去,老兄?
桃树广场饭店。杰夫对他说。
再说一次?
桃树广场,在市区。
我想我不知道那地方,有地址吗?
老天爷,现在的计程车司机怎么了?他们不该先通过考试,至少背一背城市地图和地标吗?
你知道丽晶酒店吧?凯悦饭店呢?
喔,对了,我知道。那是你要去的地方?
附近。
没问题,老兄。
计程车司机往南开了几个街区,然后在庞塞德莱昂大道右转。杰夫伸手往屁股的口袋里掏,忽然想到这件陌生裤子里可能没放钱,但他找到一个旧咖啡色皮夹,不是他的。
至少里面有钱,两张二十元、一张五元以及一些一元美钞,他不必担心付不出计程车资了。
当他把皮夹还有随手抓来穿上的旧衣服物归原主时,得记得把钱还给人家但是这些东西到底哪来的?主人是谁?
他打开皮夹里的一个小格子想找答案,发现了一张埃墨里大学的学生证,上面的名字是杰佛瑞. L.温斯顿。还找到埃墨里的图书馆借书证,一样是他的名字。得卡图路上一家干洗店的收据;一小张纸巾上面写着一个女孩名字,辛蒂,和她的电话号码;一张父母站在奥兰多老房子外的相片,在他父亲病重前,他们一直住在那里;一张彩色快照,照片里的茱蒂.高登边笑边丢着雪球,青春欢乐的脸庞裹着一圈御寒的外翻白毛领子。还有一张杰佛瑞.拉马.温斯顿的佛罗里达州驾照,有效日期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在凯悦丽晶酒店顶楼形状像个幽浮的北极星酒吧里,杰夫独自坐在一张两人座桌前,望着亚特兰大市一望无际的天际线每四十五分钟在身边旋转一圈。那位计程车司机不是没见过世面,因为七十层楼高圆柱形的桃树广场饭店根本还没盖起来。全面国际企业的高楼、由灰石块打造的乔治亚太平洋大厦,还有巨大黑盒子模样的公正大楼也都消失了。整个亚特兰大城的最高建筑就在他现在所在处,宽敞的天井式大厅有抄袭其他建筑的味道。在和女服务生闲聊了几句后,事实就很明显了,这栋饭店才刚落成,在当时仍属于十分独到的建筑风格。
最难过的时刻莫过于杰夫看见酒吧后方镜中的自己。他完全是有意这么做,他当时已经很清楚自己会是什么模样,虽说如此,当他和镜中那苍白瘦长的十八岁男孩照面时,还是震惊不已。
客观来说,镜里的男孩比实际年龄要苍老些。他在那年纪时买酒很少碰上麻烦,就像现在跟这女服务生买酒一样容易,但杰夫知道,那是因为他的身高和深陷的眼眶造成的错觉。从他自己眼中看来,镜中人不过是个未经世事历练摧折的小子。
而那个年轻人正是他自己。不是记忆中的自己,而是活在此时此地的他,是镜中那双正握着酒杯的平滑双手,那对正专注看着自己的锐利眼眸。
亲爱的,要再来一杯吗?
女服务生对他露出漂亮的笑容,复古的蜂窝头及刷上厚重睫毛膏的眼睛底下,是鲜艳的红唇。她的衣着走未来主义路线,霓虹蓝的短摆洋装看起来就像是接下来两、三年内会在年轻女性身上见到的时尚款。
从现在起的两、三年。那就是六○年代初了。
老天哪。
他不得不承认发生了什么事,不可能有别的理由了。他曾经差点死于心脏病,但被救活了。一九八八年某天,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现在却是一九六三年,而他在亚特兰大。
杰夫怎样也想不出一个合理解释,连最牵强的理由都无法说明这一切。他年轻时也读过不少科幻小说,但他曾读过的时空旅行故事情节,没有一个跟他现在的处境相像。他的故事里面没有时光机,也没有疯狂或其他毛病的科学家,而且也不像他狂热阅读的故事人物,因为他连身体都回到了年轻状态。好像只有他的心灵穿越这些年做了时空跳跃,为了在脑海中挪出空间给十八岁的自己,他的早期意识被抹消了。
他到底是死里逃生,还是只轻轻绕过死神身边?在另一个未来的时间之流中,他的遗体是否正躺在纽约某个太平间里,被病理学家的解剖刀细细切剖开来?
也许他正处于昏迷:在饱受摧残、迈向死亡的大脑命令下,绝望地编织出一个想像的新生命。然而,但是
亲爱的?女服务生询问,要我再帮你倒一杯吗?
呃,我,我想来杯咖啡,可以吗?
没问题。来杯爱尔兰咖啡?
一般咖啡就好。加点奶精,不要糖。
来自过去的女孩端上了咖啡。杰夫凝视窗外,在逐渐黯淡的天空下,半在兴建中的城市正亮起疏疏落落的灯火。
太阳消失在绵延到阿拉巴马州的红土山丘背后,仿佛也通向那动荡与巨变的年代、悲剧与梦想的年代。
冒蒸气的咖啡烫伤了他的唇,他赶紧啜一小口冰水冷却。窗外的世界不是一场梦,跟它的天真单纯一样坚实,也跟它盲目的乐观一样真实。
一九六三年春。
有那么多选择等着去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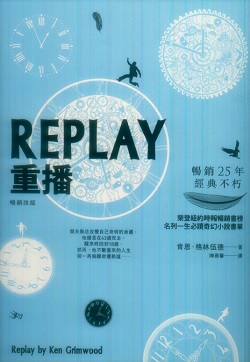
重播
肯恩.格林伍德
奇幻小说
类别- 2023-02-05发表
-
209575
已完结
© www.iabbook.com
按 “键盘左键←” 返回上一章 按 “键盘右键→” 进入下一章 按 “空格键” 向下滚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