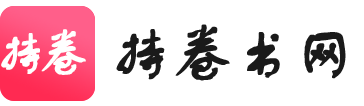阳光正在窗户上泼洒着桔黄色的写意。林徽音用目光寻找着那一对靛蓝色的小鸟,它们在窗外的竹梢上跳着、唱着,仿佛从唐诗中飞来的鸟儿,阳光梳理着它们轻灵的羽毛。有时它们便跳到窗台上来,在这个狭长的窄窄的舞台上搔首弄姿。
窗子外面是刈割过的田野,甘蔗林伐光了,稀疏的枯叶在空旷的野地里横陈,大地呈现着从未有过的宁静,欢乐和苦恼全都籽粒归仓,黛色的水牯惬意地躺在田头。
窗子的后面有孩子在跑动,孩子们永远是快乐的,孩子们快乐平凡而简单。一只小小的田螺,一只拇指大的棒棒鸟,都可以让他一直笑到甜甜的梦里。
林徽音多么羡慕窗外的一切,羡慕在窗台上舞蹈的小鸟,羡慕在窗外跑动的孩子,她也需要那么一小点儿平凡而简单的欢乐,而此刻,她却只能躺在病床上,一任阳光在窗棂上涂抹着晨昏。
从大足考察回来之后,因劳累又受了风寒,她的肺病再次复发,连续几周,高烧四十度不退。上垻村无医无药,梁思成去李庄镇请来史语所的医生为她诊治,他也学会了打针。
⊙进出当铺成例行公事
艰苦的日子伴着川南的冬天来临了,营造学社的经费几近枯竭,中美庚款基金会已不再补贴,只好靠重庆的教育部那杯水车薪的资助。
成员的工资也失去了保障,幸亏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负责人傅斯年和李济伸出援助之手,把营造学社的五人划入他们的编制,每个人才能拿到一点固定的薪水。
林徽音和梁思成两人的工资大部分都买了昂贵的药品,用在生活上的开支就拮据起来,每月开了工资,必须马上去买药、买米,通货膨胀如洪水猛兽,稍迟几天,就会化作废纸一堆。
林徽音吃得很少,身体日渐消瘦,几乎不成人形,在重庆领事馆的费正清夫妇,托人捎来一点奶粉,像吃油一样谨慎地用着,为了改善一下伙食,梁思成不得不学着蒸馒头、煮饭、做菜,他还从当地老乡那儿学会了腌菜和用桔皮做果酱。
实在没有钱用的时候,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每当站在当铺高大的柜台下面,梁思成的双腿就忍不住发抖,觉得自己的身躯在一点一点地矮下去。
留山羊胡的帐房先生,总是从那双高度近视的镜片后面,闪出一种嘲弄的目光,他只对梁思成递过来的东西感兴趣,可每一次他都把价钱压得不能再低。
梁思成拙于谈价钱,帐房先生的算盘打得飞快的时候,那声响如同一梭子弹打在他的心上,一旦拿到钱,每一次他都逃一样弹出了那家当铺。
衣服当完了,便只好把宝贝一样留下来的派克金笔和手表送到那山一样巍峨的柜台上。帐房先生对梁思成视为生命的东西,却越来越表现出冷漠和不耐烦。一支二十年日夜伴随他的金笔,一只从万里之遥的美国绮色佳购得的手表,当出的价钱只能在市场上买两条草鱼。
拿回家去,他神色凄然地说: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林徽音除了苦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唯一没有当掉的就是那架留声机了,在最艰苦的日子里,音乐成了他们的药品和粮食。
林徽音喜欢贝多芬和莫札特的作品,一曲《维也纳森林故事》、一曲《月光水仙女之舞》、一曲《胡桃夹子》,便把人带入一个奇幻的世界,只有在音乐里才能同遥远的先哲对话,让心灵听到明日的传闻,只有音乐才能让他们暂时忘掉苦难。
从这只黑色底片上旋转出来的音乐,把浸渍在盐水里的心,悄悄地冰释了。那音符是一群精灵,因为它们的降临,这两间简陋的屋子里充满了光辉。阴冷的冬天,在大面积地退去。音乐的芳香,在所有的空间弥漫着一个季节的活力。
⊙不愿向命运求抵押
更多的时候,林徽音以书为伴,雪莱和拜伦的诗伴她挨过沉默、孤寂的时光。那些诗句,一个字一个字地在她的心里生长着你那百折不挠的灵魂/天上和人间的暴风雨/怎能摧毁你的果敢和坚忍! /你给了我们有力的教训/你是一个标记,一个征象,/标志着人的命运和力量;/和你相同,人也有神的一半,/是浊流来自圣洁的源泉。
当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快要耗尽的时候,她便从这些诗句中,重新汲取到了力量,如同一个在沙漠里跋涉太久的旅人,惊喜地发现了甘泉和绿洲。
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知道了他们在李庄的困境,数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治病,同时在那里也可以找到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
林徽音和梁思成很感激老朋友的关心,他们商议后给费正清夫妇写了一封回信: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病情稍微好些的时候,林徽音便躺在小帆布床上整理资料,做读书笔记,为梁思成写作《中国建筑史》作准备,那张小小的帆布床周围总是堆满了书籍和资料。
林徽音只是从窗外景物的变化上感受着季节,夏天来临了,小屋里的气温聚然升高,闷得像蒸笼。
冰冰放了暑假,空闲下来的时候,她便教冰冰学习英语,她用的课本是一册英文《安徒生童话》。暑假结束,冰冰已经能够用英语很流畅地背诵那些故事了。
小杰也上了小学,虽然生活环境艰苦,可是这孩子的个头还是长了不少。这一年到头,他几乎是一直打着赤脚,快上学的时候,外婆才给他做了一双新布鞋。
生活就这样迈着蹒跚的步履前进。
由于营造学社的资金严重不足,对西南地区的野外考察只好停了下来。
林徽音、梁思成和大家一起商量恢复营造学社已经停了几年的社刊。
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出版刊物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李庄乡下。没有印刷设备,他们就用药水、药纸书写石印。莫宗江的才华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他把绘制那些平面、立体、刨面的墨线图一揽子包了下来。他描出的建筑图式甚至可与照片乱真。
从抄写、绘图、石印、折页、装订,学社的同仁一起动手,最紧张的时候,连家属和孩子们也都参与了劳动。一期刊物漂漂亮亮地出版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又笑又跳。
继抗战前的六期汇刊之后,第七期刊物便诞生在这两间简陋的农舍里。
纵然有时必须在命运前喘息,但充满意志的生命个体却终究不会把自己抵押给命运。有时候,命运当胸一拳,会击倒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然而,林徽音却顽强地抗争着,她甚至以写诗来表示对命运折磨的不在意。
⊙坚持自己的路
窗子外面的景色变幻着,田野重新勃发生机,雨后的甘蔗林,可以听到清脆的拨节的声音,那声音如火苗般燃烧着。棒棒鸟照旧是窗台上的客人,它们洞悉所有季节的秘密。
当林徽音把她的诗句我折一根柱枝,看下午最长的日影/要等待十一月的回答微风中吹来写在纸上的时候,阳光仍旧在窗户上泼洒着桔黄色的写意。
一九四二年,梁思成接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编写一部《中国建筑史》,这是他们还在英美留学时的夙愿,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写的建筑史。为了这部书的写作,实际上他们几年前就一直在收集资料。
林徽音的肺病越来越严重,经常大口大口地咳血,梁思成的身体也垮了下来。他的脊椎病重新复发,写作的时候,身体支撑不住头的重量,只好找一只玻璃瓶垫住下巴。
林徽音承担了《中国建筑史》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并执笔写了书中的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
这一章是全书的主干之一,共有七节,分别为:五代汴梁之建设;北宋之宫殿苑囿寺观都市;辽之都市及宫殿;金之都市宫殿佛寺;南宋之临安;五代、宋、辽、金之实物;宋、辽、金建筑特征之分析。
她介绍了宋、辽、金时代,中国宫室建筑的特点和制式,以及宗教建筑艺术,中国塔的建筑风格,辽、金桥梁建设,乃至城市布局和民居考证。
大量资料来源,是他们数年来考察中国建筑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仅是中国的塔,她就列举了苏州虎丘塔、应县木塔、灵岩寺辟支塔、开封护国寺铁色琉璃塔、晋江双石塔、玉泉寺铁塔等数百种。深文周纳地研究了它们各自的建筑风格和特点,以及宗教学意义,成为集中国塔之大成的第一部专著。
另外,林徽音还以详实的资料,分析了中国佛教殿宇的建筑艺术,对正定县文庙大成殿、辽宁义县大奉国寺大殿、山西五台佛光寺文殊殿、善化寺大雄宝殿、少林寺初祖庵大殿、江苏吴县玄妙观三清殿等数十座殿宇的建成年代、廊柱风格、斗拱结构、转角铺作诸方面进行了论证与分析。这些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工作着是美丽的。林徽音、梁思成在写作中获得了极大的快慰,倾注在创作中的时候,便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他们梦想着等战争结束了,他们的身体好起来,能再去全国各地考察。梁思成说,他做梦也想去一次敦煌,如果上帝给他以健康,他就是一步一磕头,也要磕到敦煌去。
林徽音说,她最向往的是对江南民居的考察,在南方呆这么多年,没有来得及实地考察真是太遗憾了。
⊙费正清的深刻感受
在他们的书稿即将完成的时候,费正清、陶孟和从嘉陵江搭乘小火轮溯江而上,整整四天旅程,十一月十四日来到李庄镇。费正清是专程来探望这对老朋友的。他们自一九三五年圣诞节分手以来,直到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在陪都重庆与梁思成相逢,差不多七年时间没有见过一次面。
一进门,费正清愣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几乎是原始人类穴居状态的生存条件下,这两位中国第一流的学者,虽然成了半残废,却仍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在他们的病榻周围,是堆积如山的资料和文稿。
费正清望着林徽音,心情十分激动。几年不见,竟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费正清终于忍不住说:我很赞赏你们的爱国热情,可在这样的地方做学问,也确实太难了,你们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要是美国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改善自己的生态条件,而绝不是工作。西部淘金者们,面对着金子的诱惑,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却是设法使自己有舞厅和咖啡馆。
陶孟和说:还是去兰州吧,我的夫人也在那里,西北地区干爽的空气有助于治好你的病。先把病治好了,再去写你们的书。
费正清也建议林徽音去美国治病,他可以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林徽音说:你们住上几天,也许会有另一种看法。
后来,费正清在他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一书中,感叹当年在李庄访问徽音和思成的情景: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
费正清在李庄时,大多时间因感冒在床上休息,林徽音常拿自己在李庄写的诗念给他听。费正清更感到惊奇,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林徽音居然还洋溢着诗情。
费正清退烧以后,林徽音、梁思成陪他们去外边散步,费正清对这川南小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林徽音说:中国南方的民居,最充分的体现了人文精神,我有个设想,等身体好起来的时候,要对江南民居作一番详细地考察。
费正清说:林,我已经明白了,你的事业在中国,你的根也在中国。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能移栽的植物。
⊙还乡时刻来临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贫病交加的林徽音、梁思成夫妇,欣喜若狂,八年的离乱终于结束了,好像陷进古井里的人,一下子看到了阳光。
梁思成兴致勃勃地跑到李庄镇,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买了肉和酒,还请了莫宗江一起庆祝,林徽音也开了不喝酒的戒,很痛快地饮了几杯。
乘着酒兴,梁思成大声教冰冰和小杰朗诵杜甫的诗: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随着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他们的心情也一天天不平静起来。
他们商量着,先到重庆看病,再平平安安回北平。过了几个月,营造学社的善后工作已基本办理就绪,他们搭乘史语所一辆去重庆的汽车,一大早就上路了。
到了重庆,他们找了一家比较好的教会医院,梁思成说,咱们一定把身体全面检查一下,回去路上心里也踏实。
X光检查以后,医生把梁思成叫到治疗室说:现在来太晚了,林女士肺部都已空洞,这里已经没有办法了。
梁思成如五雷轰顶,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林徽音却很坦然,安慰梁思成:现在我觉得好多了,回到北平,很快就会恢复过来。这话如一把刀子扎在梁思成心上,全身每一个器官都在流血。
从重庆回到李庄之后,林徽音的心情一直很沉重。营造学社已无法再维持下去,刘敦桢与陈明达已先后离去,留下的也人心散乱,经费来源完全中断。
梁思成觉得,中国古建筑研究,经过营造学社同仁数年努力,已基本理清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体系沿革,可以告一段落,战后最需要的是培养建设人才,特别是建筑师。他决定立即去昆明,拜会西南联大负责人梅贻琦,建议清华大学增设建筑学院。
梁思成的建议,得到梅贻琦的支持。梅贻琦答覆,首先在清华大学工学院开办建筑系,并聘他为系主任。梅贻琦还告诉他,清华大学不久就要返平,让他也做好回去的准备。
这年夏天,西南联大教工北返,林徽音、梁思成一家也跟他们一起,乘一架改装的军用飞机,由重庆回到北平。
阔别九年的故都,又重新走回林徽音的梦里。
她在心中多少次勾勒过的北平的景象,却变得扑朔迷离。前三门大街上,一辆辆十轮卡车隆隆驰过。钢铁的庞然大物,半罩炮衣,裸露着粗大的炮管,金属的冰冷仿佛要冻结盛夏的阳光。她隐约感觉,血与火的搏杀就要开始了。
⊙萧乾的欧战采访记
回到北平之后,他们把家安在了清华大学的宿舍。梁思成匆匆组建起清华大学建筑系,很快又赴美考察战后的美国建筑教育。同时,应耶鲁大学的聘请,做为期一年的讲学,教授《中国艺术史》。
战后的北平,由于经济萧条带来了物价飞涨,工商业纷纷倒闭。在他们回来的几个月内,北平的大米由法币九百元一斤,猛涨到二千六百元一斤。清华大学的学生食堂前,常常拥挤着出售衣物的学生,铺在地上的旧报纸上,用毛笔写着:卖尽身边物,暂充腹中饥。
看着那些孩子一张张菜色的脸,林徽音心中非常难过,饥饿的阴影笼罩着北平,也笼罩着清华园。清华园民主墙上,出现了反饥饿的激烈标语:饿死事大,读书事小。
林徽音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他们一家浪迹萍踪,整整九年,回来已是两手空空,带出的衣物,也在四川当光吃净。回到故都北平,贫困和饥饿仍像影子一样跟随他们而来。
一九四七年夏天,在欧洲战场饱经硝烟浸染的萧乾,由上海来北平探望老友林徽音。
当萧乾来到清华园林徽音的寓所时,老远就望见她的宅前竖了块一人高的木牌,上面写着:这里有位病人,遵医嘱需要静养,过往行人请勿喧哗。
一进门,萧乾轻轻喊了声林小姐。林徽音从屋里出来,紧紧握住萧乾的双手,眼里储满了泪水,惊喜地大声嚷着:秉干,快进屋,干嘛这么轻手轻脚的。萧乾指了指门口那块木牌。
林徽音说:你大概没想我这个需要静养的病人,一天到晚在这高声大嗓地接待客人,那块牌子是总务处写的。
坐下之后,萧乾问起了林徽音这几年在南方的生活。林徽音说:咱们早就讲好了,这一天先听你讲。
萧乾喝了口茶,讲起了他们在昆明分别后的经历。
德国并吞奥地利和捷克时,萧乾正好应聘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文系的讲师,他曾目睹过英军和德军的第一场空战。那一天是九月十五日,亦是德国空军司令戈林宣布的鹰日,伦敦市区的上空,一片黑鸦鸦的机群,机枪的扫射声,炸弹的爆炸声,仿佛把伦敦整个掀翻起来。
萧乾说:德军飞机那天轮番轰炸的时候,钢琴家缪拉.海斯和一批英国音乐家却在市中心国家艺术馆举办午餐时间音乐会,我常到那去,花上一个先令,买张入场券,一边啃面包,一边听优美的音乐,而窗外却是炸弹声和高射机枪声。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将决定这个民族的前途,这是我体会最深的一点。
⊙战争阴影未消
萧乾还谈到他在一个读诗会上,见到大诗人艾略特的情景。当时这个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正担任着伦敦防空巡逻员。读诗会的主持者是这样向大家介绍艾略特的:艾略特先生昨晚刚刚值完防空巡逻班,今天晚上可能还得值勤,他读诗的时候,要是突然打起盹来,大家要多多原谅,不过你们可别打盹。
那个晚上,艾略特朗诵了他创作的《保卫群岛》、《小吉丁》等几首诗篇。萧乾无法把眼前的艾略特同那个头戴钢盔,走在路上巡逻的艾略特联系起来。
萧乾接着又讲了他以大公报驻英国专职特派员的身份,奔赴前线采访的经历。那时盟军向莱茵河日夜逼近,直捣希特勒老巢,他平生第一次正式穿上军装,怀里揣着随军护照,上面写着:此人如被俘,须依国际联盟规定,按少校待遇。
在战场采访中,他还遇到了作家、记者海明威。他在盟军光复巴黎的战斗中,曾悄悄离开部队,组织起一支游击队,在凯旋门附近歼灭德军,救了千百个法国人的生命。巴黎战役结束后,海明威因私自参战,被送上军事法庭。
他见到海明威的时候,那个蜚声世界的大作家,在一个酒吧间里,独饮独酌,喝得很痛快,喝一口酒,便用手摸一下脸上的伤疤。
萧乾又说起德军投降后,他到美国报导联合国会议时的一段插曲。他在人行道上走着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老太太,她看着他胸前的联合国徽章,突然一把抱住他,在萧乾的脸上亲了又亲,老泪纵横地说,这下可好啦,我的乔治快回来了,我的小杰夫也不用去当兵了。当时我想,这还是战争,萧乾说完半晌,谁也没有说话。
他们整整长谈了一天。林徽音也讲了他们一家在云南、四川的离乱生活。他们各自满怀着希望盼到抗战的胜利,但中国的现状又让人感到深深的忧虑。
他们谁也无法安慰谁,他们思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