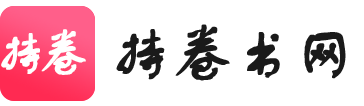第41章 附廿六、《再见度度鸟Bringing back the dodo》/Wayne Grady伟恩.葛拉帝/饶伟立翻译(二○○八年五月一日台湾商务出版)
摘自《再见度度鸟Bringing back the dodo》
●如果,绝种的dodo鸟重回人间?文/莽斯特
在自然浩大漫长的生命舞台,多少物种登场又退场,但dodo鸟可能是第一种由于人为干预而绝种的生物。一六六二年,一位遭遇船难的荷兰船员发现(并杀了)几只dodo鸟,从此以后,dodo鸟就成为一则传说与博物馆里的标本。
当dodo鸟绝种时,全欧洲只剩下两副私人珍藏的dodo鸟标本,而在收藏者身后即捐给牛津大学的爱希摩林博物馆,但dodo鸟标本无人闻问,至一七五五年该博物馆馆长终于决定将其销毁。幸好,某位有先见之明的标本制作员,留下了其中一副标本的头和一只脚,为现代遗传学家留下了一点度度鸟的DNA。如今,复制技术对于科学家已经不是天方夜谭,而若在更多充分的资料支援下,又能够取得可用的度度鸟DNA,是否就该进行再见dodo鸟计画?
让我们先把dodo鸟的问题放在一旁,听听八哥的故事。
八哥并非北美原生物种,当一八九○年代晚期,八哥从东南亚被引进加拿大温哥华之后,即使北美洲与东南亚的气候条件截然不同,温哥华的八哥数量仍然直冲云霄,甚至在一九○四年,被正式认定为本土物种之一。但八哥从一九二○年大约二万只的数量,很快地衰退到一九七一年的九百多只,甚至到了一九八五年只剩九十八只。关键就在一九五○年代起,欧洲掠鸟被引进温哥华强夺了八哥的食物,也占据最佳的筑巢点所致。而八哥引进温哥华的短短时间,虽然数量大增,却尚未演化出完全适应温哥华的生物性状与特性,因此遇上同属八哥科的欧洲掠鸟,更加速了八哥在温哥华的凋零,直至完全消失。虽然亚洲还有很多八哥存在,但在温哥华的八哥,确实是一种有如绝种的局部消失。
当某个物种绝种后,其他物种便会填补该物种在生态系所占据的地位或位置,当dodo鸟绝种时,大自然也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这个生态真空,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凭借人力而使dodo鸟重回人间,将有人力无法估算的生态失衡,而且复制重生的dodo鸟族群,也可能因为复制最初的细胞核缺陷,使重生的族群在短时间再次灭绝。
●序/Wayne Grady伟恩.葛拉帝
五年前,《探索》(Explore)杂志的大无畏编辑李陀(James Little)邀请我为这本杂志定期撰写专栏,希望我能担起加拿大的逵曼(David Quammen)这个重责大任。逵曼是美国自然学家,多年来一直为《户外》(Outdoor)杂志撰写自然史专栏。李陀的建议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我一向自诩是加拿大的麦克菲。但适应是生命的本质,因此我便毅然接下了这项挑战。我非常高兴自己当时如此决定。
撰写这个专栏让我得以从崭新的观点,思考人类这个物种的点点滴滴。这个专栏的构想是由自然史的角度,检视当代的生活型态。我的职责则是以业余自然学家的身分,每两个月撰写一篇文章,探索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物。这个专栏名为<生物二三事>(Biologic),我总共为它写了十五篇文章,每篇长约二千五百字。对专栏而言,这些文章稍嫌过长,但我很幸运能有足够的空间,思考各个看似殊异的议题之间的可能关联,并尝试从中萃取出井然有序的结论。李陀让我自由地探索科学、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他为某些文章的主题提供了宝贵的建议。读者来信提及的各种轶闻趣事,则为其他文章提供更多灵感。这些文章就在<生物二三事>为时二年半的生命里,逐渐演化成这本拥有一致主题,但也兼容并蓄的散文集。
事实上,这些文章比较像是刚成形的散文。有些学者主张,专栏文集必须忠实复刻原本刊登的文章,不可修改其缺陷、错误,以及过时的参考资料等。不过,我并非此道中人。专栏文章不是散文。专栏文章必须在读者稍纵即逝的阅读兴趣、固定或极短的截稿期限,以及无法通融的长度规定等限制下完成,但散文却只能在较为宽容的写作条件下,才能兴盛开展。
在本书里,我以认真勤奋的园丁为师,将这些专栏文章从它们萌芽的苗圃《探索》杂志的页面逐一掘出,再定植至较为持久的花床上。我补充了一些资讯,更新了一些资料,修改了某些段落,甚至新增了两篇文章。 (<爱特伍和麦克基本>是从我对爱特伍(Margaret Atwood)的小说《末世男女》(Oryx and Crake)的书评扩增而来的;这篇书评原本刊登在《渥太华公民报》(Ottawa Citizen)。<复制人来了>则梳理出前面几篇文章里的一些想法。)我也更正了我(以及其他人)发现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多篇文章的主题,并尝试借着这些文章,传达出一位时间充裕,心灵澄澈的作者,在深入思考这个专栏触及的议题后,最后发展出来的成熟想法。我希望这种种努力,最后能够造就出一本主旨明确,融贯一致的文集。
本书的主旨是什么?假如只需区区几字便能说明本书的主旨,那么这些文章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这么说并非刻意造作,或故意含糊其词。如同所有读者一般,我也只有在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后,才能领略贯穿其间的主题。我想我在这些文章里试图突显出,我们忽略或否认我们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倾向。正如十九世纪人类学始祖布鲁门巴赫(J.F.Blumenbach)一般,我也相信我们是最为驯化的物种,而这正是本书的基础观点。不过,我们并未将自然从我们之间抹除即使是最为驯化的家猫也会吃喝、呼吸、猎食、长虱子,以及繁衍后代相反地,是我们将自己从自然里抽离了出来。
在本书里,我试图点出下列这项事实:破坏自然不论是伐林造路、狩猎自娱,或消灭害虫即是放弃人性。不论是经由修改生物基因创造新生物,以人工复制或基因剪接取代有性生殖,或从生态系统移除或增加某个物种,我们一旦介入自然,随即会对它造成干扰。亿万年来,自然孜孜不倦地守护着我们,而我们却对它毫无所悉。我们必须谨记,当我们在森林里遇到野熊时,它对我们的了解,远远超过我们对它的了解。
但是,我并不擅于滔滔雄辩。我只是想以自然为脉络,反思我们这个物种的作为,并探询我们持续如此的原因。假如我的语调听来忧心忡忡、不可思议,亦或毫无耐心,我只能说这是作家的通病。文章就像珍珠一般,两者皆源于一颗扰人的沙粒。
●第十三章:再见dodo鸟/Wayne Grady伟恩.葛拉帝
dodo鸟的叫声,
这种我愿意倾听的声音,
有如不曾存在的言语,
可惜只有少数人懂得。
乔治.约翰史东<度弗福路鸟>
身为科幻作家,艾西莫夫(Isaac Asimov)擅长前瞻未来;而作为科学家,他对过去也多有真知灼见。他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基因密码》(The Genetic Code)里,巧妙地融合了这两个面向,探索DNA的发现过程,并深究我们对生命运作原理的认识。在反省几项重要科学发现和其渗透人类日常生活的轨迹后,他发现科学在短时间内即可改变人类社会。重大的科学突破,他写道:大约只需六十年即可开花结果。举例来说,丹麦科学家厄斯特(Hans Christian Oersted)于一八二○年发现电磁作用后,人们即在一八八○年以此为基础,制造出白炽灯泡;爱迪生于一八八三年观察到电能从灯丝转移至金属板上的现象后,我们也在一九四○年代早期以此为基础,发明出电视和电脑萤幕。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九四四年时,任职于纽约洛克斐勒医院的加拿大裔生物学家艾弗里(Oswald T.Avery),分离出一种能转换细菌菌株的物质。这种物质就是简称为DNA的去氧核糖核酸。艾弗里不是去氧核糖核酸的发现者他只是针对英国病理学家格律菲斯于一九二○年代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继续后续研究而已但他是首位提出去氧核糖核酸(而非如前人想法所指的蛋白质)才是影响遗传性状的物质,也是所有生命基础的科学家。这个发现改变了我们对生命的认知。从此以后,生命不再是控制我们的力量,而是我们能依据自己的需求予以操弄的分子组合。不论我们如何使用这种能力,艾西莫夫预测在艾弗里这项发现的六十年后,遗传学将出现一场巨大变革。艾西莫夫写道:假如届时我们依然存在,二○○四年将是分子生物学名留青史的一年。
假设艾西莫夫所言大致正确科学家经常在某些误差范围内进行研究,他们将这种误差称为修正系数再假设遗传学将在近年内出现重大突破(华生(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直到一九五三年才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所以我们可多给艾西莫夫十年),那么,有趣的问题则是:遗传学将会出现哪些重大突破?完成人类基因组图谱看似堪称突破,但它其实较像是重大变革的前奏,而较不像是真正的典范转移。
人类基因组图谱让人们得以看见典范转移的前景:遗传学家早已开始讨论如何藉由辨识和操弄特定基因,让我们的后代拥有各种可欲但无法界定的特质(例如,美丽、聪明和健康等)。这种美其名为种系疗法(germline therapy)的想法,其实无异于死灰复燃的优生学。高腾(Francis Galton)于十九世纪晚期率先提出的优生学,经过纳粹德国的滥用后,早已被世人所唾弃。虽然种系疗法的确算得上是遗传学的重大突破,但由于受到许多人的反对包括教宗和美国总统它似乎不可能在艾西莫夫的预言到期前实现。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蒙德尔森(Everett Mendelsohn)最近即指出:一九五三年萌芽的基因革命,不论是在科学上或文化上,都不太可能于二○五三年,我们的子孙庆祝其诞生一百周年时完成。
那么复制(cloning)呢?复制其实也不是新把戏了,至少就复制动物而言的确如此。早在一九五一年,也就是艾弗里划世纪发现后的第七年(而非第六十年),世上第一只复制动物(一只青蛙)即已诞生。当时的科学家先将某个青蛙卵子的细胞核移除,再把取自另一只青蛙细胞的细胞核,植入这个失去细胞核的卵子里,最后让拥有新细胞核的卵子依正常程序发展,直到长成蝌蚪为止。这些科学家总共进行了一百九十七次细胞核移植,并复制出二十七个存活至蝌蚪阶段的胚胎。这种高成功率着实令人印象深刻。四十年后,复制桃莉羊的科学家进行了数千次尝试后,才成功地复制出一个胚胎。不过,自桃莉羊诞生后,基因技术人员已经复制出许多动物,包括猪、山羊、牛、老鼠和白尾鹿等。除此之外,科学家也开始着手复制濒危动物二○○一年一月,一只名叫贝丝(Bessie)的代理孕牛,即在俄亥俄州生出了一头复制印度野牛;纽奥良的奥杜邦动物园,也豢养着一只复制非洲猫。
还有哪些遗传学突破等着科学家实现?近在眼前的可能性之一,便是尝试复制早已绝种的生物。
《侏罗纪公园》将这种可能性描绘得淋漓尽致,而其根据是一部科幻小说。一如艾西莫夫,这本小说的作者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也擅长根据合情合理的科学原则,建构出曲折离奇的科幻情节。他以假定为真的书写方式,引介各种虽具争议但也不无道理的科学假设。克莱顿撰写《侏罗纪公园》时,一般人尚不认为恐龙是集中产卵且会照顾后代的群居生物,有如克莱顿在书中的描述一般。但这些假设现在皆已被视为有凭有据的科学理论。
理论上说来,科学家可从远古的蜥蜴基因库中,萃取出恐龙基因的想法也不无可能,问题在于科学家从未发现类似的基因库。在克莱顿的笔下,科学家在一块八千万年前由树汁凝固而成的琥珀里,发现了一只血液里带有恐龙基因的蚊子化石。而在真实世界里,科学家也已能自类似的标本来源,取得古老的去氧核糖核酸。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人员波纳尔(George Poinar),即曾由一小块黎巴嫩琥珀里,萃取出一亿二千五百万年前的甲虫基因片段。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曾发现过恐龙的血液样本。科学家有天或许将从亚伯达省的沥青砂坑,挖出保存良好且尚未变成化石的恐龙遗骸。仍可燃烧的白垩纪木块就曾因此重见天日,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可能找到鸭嘴龙的后腿组织?不过,恐龙生存的年代距我们极为遥远,这使我们发现恐龙基因的机率变得微乎其微。
那么比恐龙晚一点绝种的生物呢?一九九七年时,西伯利亚北部的一个家庭,发现了一只仍带着毛皮的长毛象(Mammuthus primigenus)遗骸。这个发现让生物复制专家兴奋不已,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只长毛象被冰封在喀拉海(Kara Sea)附近的冰河里。它的头盖骨上方暴露在空气中,而其脑部多半都已不见,但其他部分则完好如初,有如它在二万零三百八十年前冻死当天一般地完整。长毛象是现代亚洲象和非洲象的直系祖先,生活于四百万年前的地球上,直到一万一千多年前威斯康辛冰河期结束为止。
多年来,科学家在北极不断掘出零碎的长毛象化石。据估计,西伯利亚的永冻土里,大约埋有一千万副长毛象化石,而北美洲的长毛象化石数量更是惊人。我认识一位住在育空地区道森市(Dawson City)的退休矿工。他即曾从永冻土的漂砂矿里,挖出十几支长毛象象牙、牙齿和骨头。他将较完整的化石捐给渥太华的自然史博物馆,并把他留下的零碎长毛象化石,以及绝种驯鹿和野牛的化石,整齐地摆在餐桌上供我欣赏。他的收藏虽然迷人,但对我而言,这些化石本身却显得死气沉沉,令我不禁怀疑我们是否能从化石里萃取出堪用的去氧核糖核酸。
但那只名叫札可夫(Zharkov)的西伯利亚长毛象,简直就像一大块刚过保存期限的肉块。闻讯赶到现场的荷兰科学家布格(Bernard Buigues),小心翼翼地将整只长毛象连同二十三吨的冰块从冰河里掘出,运到两百五十公里之外的卡丹加市(Khatanga),然后以吹风机慢慢融化包裹着长毛象的冰块。长达一公尺而卷曲的粗厚象毛充满生气,柏格表示,而他的工作室里则弥漫着令人永志难忘的浓密长毛象气味。研究团队成员摩尔(Dick Moll)将这个发现形容为美梦成真。
摩尔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这具遗骸是否含有可用来复制长毛象的去氧核糖核酸。而他对此充满信心。我们所必须找到的,他说道:是藏在股骨等大骨骨髓,或柔软器官里的去氧核糖核酸。
不过,经过一年的烘干程序后,圣彼得堡动物学院生物学家提可诺夫(Alexei Tikhonov)却宣称,从札可夫身上复制出长毛象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水伤、冰冻融解循环、紫外线辐射,以及化学衰变等,都会对包裹去氧核糖核酸的脆弱细胞壁造成损害。自札可夫身上萃取出来的一小段基因,让科学家得以在长毛象和现代象之间建立更详细的血缘关系,并得知它们突然绝种的原因(在长毛象最后几千年的生命史里,类似(?)疹的疾病可能导致其数量急速下降。现代印度象仍是这种疾病的带原者,而非洲象仍会死于这种疾病)。但我们还是不太可能在墓碑国家公园(Tombstone National Park),看见正在原野上漫步的长毛象。
(一群尚未死心的日本科学家,则试图从另一只一九九四年发现的长毛象身上萃取出去氧核糖核酸。这些科学家希望能以前者经过修补的精子,让一只印度象受孕。假如他们的尝试成功,他们计画在西伯利亚科雷马河(River Kolyma)附近的冰河时期主题公园,展出这只拥有百分之八十八长毛象基因的大象。)
由于去氧核糖核酸在生物死后,随即停止自我修护并逐渐分解,因此科学家纷纷将希望转移至比长毛象更晚绝种的生物。
符合资格的生物数量繁多,且有与日俱增的倾向,而这一切都拜我们所赐。自工业革命以来,物种即以等差级数的速率不断灭绝。
一八○○年至一八五○年间,只有两种哺乳类由于人为因素绝种,即北美洲的东部野牛(eastern bison),和西印度群岛的希斯潘诺拉乌提亚硬毛鼠(Hispaniola hutia)。
一八五一年到一九○○年间,共有三十一种哺乳类绝种,包括一种名为夸卡(quagga,又名白氏斑马)的迷人南非斑马。
而在一九○一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又有四十种哺乳类自世上消失,包括非洲狮、日本狼和德州灰熊等。目前全球约有超过六百种哺乳类,以及无数的鸟类、鱼类、昆虫和植物濒临灭亡边缘。不消多久,科学家就再也不愁找不到可供复制的绝种生物。
事实上,目前至少有两项复制计画,与刚绝种不久的生物有关。科学家正忙着复制西班牙山羊和袋狼。在世上最后一只西班牙山羊死前一年,科学家从它身上取得了一些活体组织。但我们还不知道是否能自这些组织中,萃取出足够复制所需的去氧核糖核酸。 (这只名叫西莉亚(Celia)的山羊,在一九九八年被倒下的树压死。)
袋狼也面临相同的处境。虽然传闻指出袋狼仍在塔斯马尼亚的偏远地区出没(一如东部美洲狮),但澳洲遗传学家则将希望寄托于一个自一八六六年,即一直保存在酒精里的袋狼胚胎。这些科学家预计花费至少十年的时间,检验这个胚胎是否具有可用的去氧核糖核酸,但假如他们成功的话,《环球邮报》的科学记者麦罗伊(Anne McIlroy)最近指出:
步上dodo鸟后尘(going the way of the dodo)这句话将重新定义。
逝者如dodo鸟(dead as the dodo)意指消逝已久、无须多想的事物。
但有些过去的事物,免不了仍会偶尔盘据我们心中。 dodo鸟也是如此。事实上,从它们所拥有的象征意义来说,dodo鸟(Raphus cucullatus)不愧是最值得复制的物种。而从表面上看来,复制dodo鸟的成功机率,似乎也不亚于复制西班牙山羊或袋狼。
dodo鸟原生于印度洋上距马达加斯加岛不远的马斯克林群岛(Mascerene Islands)。它们的体型巨大、无法飞行,且性格呆若木鸡(其原名dodo可能源自葡萄牙文里意指呆子的doudo),同时也是鸽子的近亲。
一五九八年,荷兰舰队司令范尼克(Jacob Cornelius van Neck)麾下的一艘船舰,在登陆马斯克林群岛里最大的模里西斯岛(Mauritius)取水时,发现岛上满山遍野的dodo鸟。范尼克将它们称为walghvogels,意指令人作恶的鸟。他曾写道:这些鸟煮得愈久,其肉质便变得愈硬,且愈难以下咽。
不论如何,接下来的四十年里,dodo鸟肉一直都是东印度公司船员的生活必需品。荷兰人在模里西斯岛上建立殖民地后,不但随意捕杀dodo鸟,腌制鸟肉卖给路过的商船,更在当地引进猪和猴子,任由它们猎食dodo鸟及其鸟蛋。持续多年的屠杀,终于将dodo鸟赶尽杀绝。一六三八年时,东印度公司船长曼迪(Peter Mundy)指出,一年前他还在模里西斯岛上看见一些dodo鸟,但这次返航时却一只都没有见到。一六六二年,一位遭遇船难的荷兰船员发现(并杀了)几只dodo鸟。从此以后,便再也没有人见过dodo鸟。
自然学家逵曼在《dodo鸟之歌》(The Song of the Dodo)里指出,dodo鸟可能是第一种由于直接人为干预而绝种的生物。他写道:dodo鸟是绝种鸟类中的传奇。而了解人类在这个传奇里所扮演的角色,则象征着人类意识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觉醒时刻。假如我们果真能使dodo鸟死而复生,我们不但可以弥补过去犯下的一个大错,也将能为逆转其他人为遗憾带来一丝希望。艾西莫夫对此必会深表赞同。而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小段去氧核糖核酸。
不过,事情没有如此简单。 dodo鸟绝种时,全欧洲只剩下两副dodo鸟标本,由热爱奇异鸟类的英国自然学家特斯德拉坎特(John Tradescant)珍藏。一六三八年特斯德拉坎特去世后,这些标本被捐给牛津大学的爱希摩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过着无人闻问的日子,直到一七五五年该博物馆馆长决定将其销毁为止。幸好,某位有先见之明的标本制作员,留下了其中一副标本的头和一只脚,为现代遗传学家留下了一点dodo鸟的去氧核糖核酸。
一八六三年自模里西斯岛上河床出土的dodo鸟骸骨(现藏于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和斯密生学会),也是可能的去氧核糖核酸来源。佛罗伦斯大学自然史博物馆里,则收藏了dodo鸟头部。而我则有幸看过这颗有如从白垩雕刻出来的头颅。它比我在道森市所见的长毛象看来更无生气。
一九六一年时,著名的耶鲁大学生物学家哈钦森曾预测:未来我们的确可能发现蛋白质含量充分的骨头化石,得以对度度鸟的亲缘关系进行免疫测试。但很明显地,我们不应在资料相较之下显得稀有的情况下进行实验,而应等到技术细节较目前更为完备时,再开始着手研究。目前的技术细节,的确已较当时更为完备。一组荷兰研究团队最近(二○○五年十月)在模里西斯岛上的沼泽里,发现了七百余支dodo鸟骨。不过,这些骨头虽能协助我们鉴别度度鸟和鸽子之间的血缘关系,但科学家并不奢望其中包含任何可用的去氧核糖核酸。
然而,这世上还有一种绝种生物可供科学家复制。这种生物不但绝种不久,其栖地也离我们较近。它们就是曾生活在美洲东北部沿岸的大海雀(great auk,学名为Alca impennis)。
大海雀是海雀(puffin)和海鸠(guillemot)的近亲,但体型大上许多。大海雀在许多方面与dodo鸟颇为相似:它们都不会飞行、行动笨拙、极易捕杀,且住在岛上。大海雀通常独居,但繁殖期会在拉布拉多(Labrador)、纽芬兰岛、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地附近的多石岛屿上,形成数百万计的聚落。水手只要带着棍棒和麻袋,不出一个钟头,即可捉到数百只大海雀。
大海雀长着暗棕色的鸟喙,胸腹呈白色,眼睛和鸟喙之间,亦有白色色块,其他部位则呈黑色。盖尔语将之称为gaerrabhul,意指粗壮有力,带着斑点的鸟。这也许是维京人和后来的英国渔夫,分别将大海雀称为geirfugl和garefowl的原因。凯尔特人称这些大鸟为Pen|gwyn,意指白头。而德雷克爵士之后则援引这个字,指称生活于南极的企鹅。
许多早期记载显示,人们曾在大海雀繁殖的地点大肆捕杀这些鸟类:船舱里堆满了腌制的大海雀肉,以及用海带包裹的鸟蛋。很明显地,大海雀比度度鸟好吃多了。西元一千年时,欧洲大西洋沿岸已难以见到大海雀。但一五三四年时,卡波特在纽芬兰的芬克岛(Funk Island)上,发现广大的大海雀栖地(芬克岛或许就是因大海雀散发出来的臭味而得名:芬克岛闻起来就像死神一样。法兰克林.罗素(Franklin Russell)如此写道)。
大海雀早已从芬克岛上消失,现在岛上住着大约一百万只海鸦(murre)。十七世纪时,人们利用大海雀羽毛制床,并以其油脂作为灯油和炉子的燃料,导致大海雀数量持续减少。一八二一年后,纽芬兰岛上已见不到大海雀。而一八三○年时,冰岛附近一座火山爆发,导致一座栖息着大海雀的小岛沉入水中,只有五十只大海雀侥幸飞抵邻近的艾尔迪岛(Eldey Island)。当全球各地博物馆明白大海雀数量已所剩无几后,纷纷开始以高价抢购其标本。这世上的最后五十只大海雀因而逐一遭到杀害,并制成标本出售。
奥杜邦从未见过活生生的大海雀,而其著名的大海雀画像,其实是临摹标本而来。一八四四年时,艾尔迪岛上只剩下两只大海雀。同年六月四日,三位冰岛渔夫将船划至岛上,并杀了这两只大鸟。
不过,一八六三年时,一位粪磷矿矿工在纽芬兰的企鹅岛(Penguin Island)上,发现一堆埋在黏鸟胶里的大海雀冰冻残骸。这些残骸很快即被送至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目前,全世界约有八十副完整的大海雀标本,以及无数的大海雀骨骼和鸟蛋标本,应能提供复制大海雀所需的去氧核糖核酸。身为加拿大dodo鸟的大海雀,可望成为第一种死而复生的加拿大鸟类。
缺乏代理孕母所引发的问题,也将dodo鸟排除在适合复制的生物名单之外。试问这世上有哪些鸟类,能充当dodo鸟胚胎的孕母呢?
复制之所以能成功,有赖科学家将重新植入细胞核的卵子置入孕母的子宫里,且孕母最好与胚胎来源物种同科或同属。
最近,科学家在复制非洲野猫(Felis sylvestris lybica)时,即采用与其同种的家猫(Felis sylvestris catus)作为孕母。倘若我们想让袋狼(Thylacinus cynocephalus)重返人间,则得仰赖同属肉食有袋哺乳动物的袋獾(Sarcophilus harrisii)。假如能取得更多去氧核糖核酸,长毛象也能以非洲象或印度象作为代理孕母。
但哪些鸟类能协助可怜的dodo鸟重现人世?孤鸽(solitaire)是最后一种孤鸽科(Raphidae,鸠鸽科(Columbidae)亚科之一)成员,但其数量也非常稀少。
逵曼指出,雷尼旺(Reunion)和罗德里格斯(Rodrigues)两个岛屿上,曾住着无法飞行的大型孤鸽(雷尼旺岛上的孤鸽学名为Ornithaptera solitaria,罗德里格斯岛上的孤鸽学名是Pezophaps soliotaria),而一如dodo鸟,这些孤鸽的血缘也与鸽子相近,但两者亦皆已绝种。至于坦氏孤鸫(Myadestes townsendi)则是一种北美鸫鸟,因此绝对无法作为dodo鸟的孕母。
粉红鸽(Nesoeanas mayeri)或许是次佳的选择。模里西斯岛上仍可见到这种鸟,但为数不多,且已接近绝种边缘。我们也许须先复制粉红鸽,等到有了稳定的dodo鸟孕母来源,才能开始尝试复制dodo鸟。
(某些鸟类学家认为dodo鸟与秧鸡的血缘较为接近。果真如此的话,可能作为dodo鸟孕母的鸟类就多了许多。纽西兰的南秧鸟(Notornis)是世上最大的无法飞行秧鸡。一如dodo鸟,南秧鸟每次只产一颗白色鸟蛋,而鸽子每次则可产下数个带有斑点的蛋。)
相较之下,大海雀仍有许多近亲活在世上。刀嘴海雀(Alca torda)即是其中一种。刀嘴海雀的体型虽较为娇小,但至少与海鸦和海雀同是海雀科(Alcidae)的一员。若有必要的话,某种南极企鹅也可充当大海雀的孕母,虽然这些鸟儿的前途亦不明朗。
许多环保人士提出一个比我们是否能复制绝种生物更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该尝试让消失已久或濒临绝种的生物重回人间?虽然亲眼目睹dodo鸟和大海雀真实模样的可能性令人神往,而再也不需担心穴鸮即将绝种的安全感也让人放心,但复制绝种生物的做法也非毫无争议。环保先驱布劳尔即反对将仅存的几只野生加州兀鹫关进动物园里,并以人工繁殖延续其命脉。他不忍见到一度繁盛的濒临绝种动物,在动物园中藉由布偶学习觅食,而肛门里也被植入无线电发射器。他认为我们应让逐渐凋零的物种带着尊严死去。最后,加州兀鹫仍被关进动物园里,人工繁殖的成鸟也被野放,整个物种虽因而得救,但其天然栖地却已被人破坏殆尽。尽管加州兀鹫因此再度翱翔于天地之间,但徒步旅行者却较有可能在亚历桑纳州的帕利亚峡谷|佛密良悬崖荒野保留区(Paria Canyon|Vermilion Cliffs Wilderness)看到它们,而非在其原生地加州看到它们。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说,让绝种生物起死回生的尝试也非好主意。我们都知道自然处理生态真空的方式:当某个物种绝种后,其他物种马上会填补其生态位。所以当大海雀自世上消失后,其繁殖和觅食地点即被海鸦、刀嘴海雀、海雀和海鸠等海鸟所占据。在这种情况下让大海雀重回人间,无异于引进与上述海鸟竞争有限生存空间的新物种,使大海雀成为海上的欧洲掠鸟。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再次冒险干预我们所知不多的生态系统。
经由复制诞生的生物,将是生物多样性流失的终极象征。
最近,我在偏远地区的一家旅馆吃早餐时,不禁觉得钉在墙上的六具白尾鹿头标本,正整齐划一地以它们的玻璃眼珠瞪着我看。而让我在大口咀嚼基因改造玉米片时大感惊讶的是,这六个鹿头看来几乎一模一样。毫无疑问地,这些鹿都在当地被射杀,因此必定来自颇为局限的基因库,或许也都与彼此拥有相近的血缘关系。在同一群复制生物里,每只生物都将拥有一模一样的基因:换句话说,假如某只生物患有遗传疾病,其他生物也将无法幸免于难。人类之所以能在地球上生存如此久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我们不断地藉由不同族群之间的通婚,提升整体人类的生物多样性。这让许多人拥有对抗黑死病或禽流感的免疫力,足以抵抗这些流行病,继续繁衍人类的血脉。但复制生物并不具备这种特质。倘若细胞核捐赠者的心脏有毛病,或不幸无法适应环境,整个复制族群也都将面临同样的困境。
我们也许该向上天祷告,祈求艾西莫夫的预言没有实现的一天。我们或许不需遗传学上的突破。对动物进行复制,也许只是复制人类的前奏,因此并非我们应该踏上的道路。艾西莫夫提醒人们:这种新知识可能遭到误用,而科学控制生命的企图,也可能成为全新的恐怖根源。
桃莉羊死于二○○三年二月十四日情人节当天。由于它诞生于爱丁堡的罗斯林研究所(Roslin Institute),因此死后即被捐给国立苏格兰博物馆,并在那里被制成标本,以便公开展示。我们也许应在桃莉羊身边摆上一具dodo鸟标本,以及一些大海雀、旅鸽、白氏斑马,和其他绝种生物的标本,好让它们能齐聚一堂,并为我们上一堂课。这堂课的名称,就叫做人类从未记取的教训。
⊙罗德里格斯渡渡鸟Pezophaps solitaria。样子像渡渡鸟,跟渡渡鸟一样不会飞行,渡渡鸟的一种。一七三○年灭绝。
科学分类
界:动物界Animalia
门:脊索动物门Chordata
纲:鸟纲Aves
目:鸽形目Columbiformes
科:鸠鸽科Columbidae
属:Pezophaps(Strickland,一八四八年)
种:罗德里格斯渡渡鸟P.solitaria
二名法:Pezophaps solitaria(Gmelin,一七八九年)
⊙留尼旺孤鸽(Threskiornis solitarius),又名留尼旺渡渡鸟,是留尼旺已灭绝的特有种。它们有可能就是葡萄牙水手于一六一三年所发现的同一种渡渡鸟(Raphus solitarius)。
留尼旺孤鸽最初是由Edmund de Selys|Longchamps于一八四八年所描述,但其存在要到二十世纪末在留尼旺发现了其骨头才得到确定。这些骨头确定了它其实是一种朱鹭,并与早期探险家所述符合。
留尼旺孤鸽独自生活在森林中,它们吃蠕虫及甲壳类等无脊椎动物。若受到威胁,它们会奔跑逃走,以双翼滑翔一段短距离。它的羽毛呈白色,翼尖及尾巴呈黑色,头部没有羽毛。它的喙及脚都很长,喙稍微向下弯。它们的外观像双翼较短的埃及圣鹭。
留尼旺孤鸽的最后纪录是一七○五年。十八世纪初灭绝。
科学分类
界:动物界Animalia
门:脊索动物门Chordata
纲:鸟纲Aves
目:鹳形目Ciconiiformes
科:(环去王+鸟ㄒㄩㄢ)科Threskiornithidae
属:(环去王+鸟)属Threskiornis
种:留尼旺孤鸽T. solitarius
二名法:Threskiornis solitarius(Selys,一八四八年)
异名:Raphus solitarius。 Victoriornis imperialis。 Borbonibis latipes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