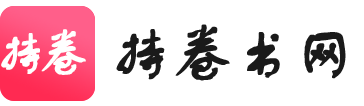多年前,还是小孩子的时节,在他那个尽力维持正常模样的家里,他父母周六晚上经常出去跳舞。他看着他们收拾准备;如果他待得够晚没睡,之后也可以追问他母亲。可是渥斯特城中那家梅森旅社的跳舞厅里,到底是怎么个状况,他却从没机会目睹:他父母都跳些什么舞,跳时是否假装深深凝视对方眼眸,他们是不是只跟彼此跳,或还是像美国电影里面一样,陌生人可以把手放在女士肩上,便将她从原来的舞伴身边带走,剩下那个人,就只好为自己去另寻舞伴,不然就只有独自站在墙角,闷闷不乐地抽着烟。
都已经结婚了,为什么还要那么麻烦,穿衣打扮跑到饭店里去跳舞,明明可以在自家客厅,跟着收音机里的音乐起舞,同样可以跳得高高兴兴,他真不懂为什么。可是对他母亲来说,周六晚上这梅森旅社的时光显然相当重要,重要到跟可以自由自在,爱骑马就骑马,或者若没有马,自由骑单车一般重要。跳舞、骑马,根据她对自己人生的说法,代表她婚前原有的生活,在她变成囚犯以前。 (我绝不做这屋子里的囚犯!)
她这番坚决心意,结果都是白费。也不知是他父亲办公室里哪个人,原先周六跳舞时让他们搭便车的,这人后来搬家了还是怎么地不再去了。那件亮闪闪的蓝色衣裳,上面那只银别针,那双白色手套,那顶侧戴在她头上的有趣小帽子,便都从此消失到衣橱和屉柜里去了,就这样。
至于他自己,他很高兴这跳舞一事终告结束,虽然他并没有说出来。他不喜欢他母亲出去,不喜欢第二天她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情。而且跳舞本身,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凡是宣传有跳舞内容的电影,他都敬谢不敏,那些人脸上那种傻兮兮的多情表情,他可不敢领教。
跳舞是个好运动,他母亲坚持。可以教你韵律感还有平衡。他可没被说服。如果需要运动,大可做柔软体操,举举重,或绕着邻里街道跑啊什么的。
离开渥斯特以后多年之间,他对跳舞的看法依然不改。大学时,他发现去参加派对却竟然不会跳舞实在太糗了,因此自己掏腰包,报名一家跳舞学校的套装课程:快步、华尔滋、扭扭、恰恰。但是没有用:不到几个月他就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一种有意的忘记。为什么会这样,他清楚得很。他从没有过一时半刻,甚至在上跳舞课的时候,曾将自己真正地投入舞中。虽然他的脚跟着舞步,内在却始终僵硬,始终在抗拒。就这样,现在依然如此;在最深处,他实在看不出为什么人们需要跳舞。
跳舞这事,只有在诠释成另一件事的时候才有意义,却是大家不愿意承认的那件事。而那另一件事,才是真的事:跳舞本身,只不过是掩饰的借口。邀女孩子去跳舞,意味着邀她去交媾;而接受这个邀请,则也意味着她同意去交媾;跳舞本身,是个哑剧,是交媾的前奏。其中的呼应如此明显,他真不懂大家为什么还要费事地去跳什么舞。那么不怕麻烦地穿衣打扮,那么些仪式动作;干什么弄出那么一大套虚礼?
老式舞曲的音乐,带着它那种土气呆滞的节奏,梅森旅社里的那式音乐,一向令他觉得沉闷。但是美国来的那种没教养的音乐,他自己这个年纪的人现在跟着跳的,他也只觉得总看不顾眼,不对味得很。
南非老家收音机里播放的歌,也都是美国来的。报上成天追踪报导美国电影明星那些稀奇古怪的行为,众人疯魔似地跟着,至于呼拉圈之类的美国流行热,大家也像奴才似地一味盲从。干什么呀?为什么凡事都要跟着美国?先是被荷兰离弃,现在又遭不列颠断绝关系,南非人是不是已经打定主意,决定要变成冒牌美国人了?虽然他们这辈子,多数都从没见过半个真正的美国人。
原本他还以为,到了不列颠总算可以甩掉美国了摆脱掉美国音乐、美国流行热。没想到可令他丧气极了,不列颠人模仿美国的狂热程度竟然不下于南非。大众报纸上刊登着女孩子在演唱会上死命尖叫的照片。男生留着及肩长发,用冒牌的美国口音嘶吼呻吟,接着把自己的吉他用力砸碎。他简直没法忍受。
还好不列颠有个第三台,解救的恩典。如果在IBM工作一天下来,有一事是他期待的,那就是回到他一屋的安静,扭开收音机,请这些他从没听过的音乐来访,或是那些冷静、智慧的谈话。夜复一夜,从不缺席,也不花他半毛钱,只要他去触碰一下,这些大门就应声开启。
第三台广播只有长波。要是第三台也在短波上发送,当初他在南非也许早就听到了。那样的话,还需要千里迢迢跑到伦敦来吗?
诗人与诗系列节目里面,有一回谈到一个俄国人叫约瑟夫.布罗茨基【注一】。布罗茨基被控是社会寄生虫,判往冰天冻地的北方,阿尔汉格尔斯克【注二】半岛上的劳工营服五年苦役。目前仍在服刑当中。想想看,就在此时,当他坐在他伦敦的温暖房间,啜着他的咖啡,小口咬着葡萄干坚果甜点的同时,却有一个人,年纪同他一般,也像他一样是个诗人,整天伐锯着木头,照护着冻疮的手指,用破布头补缀着他的靴子,只有鱼头和卷心菜汤可吃。
【译注一】Joseph Brodsky,一九四〇︱一九九六,一九七二年离开俄国,流亡美、英。一九八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译注二】Archangel,前苏联西部一港市,濒临白海。
幽暗如针之内布罗茨基一首诗里写道。他没法把这行诗从脑中赶出。如果他能专心一点,真正地集中心神,夜复一夜,即使就只靠全神贯注,强迫灵感的祝福临到他,也许,他也能写出点什么像样东西,可以跟这一句相称。因为他里面也有那东西,他知道,他所拥有的想像力,与布罗茨基属于同一色调。可是写好之后,又怎样才能把话传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呢?
就根据他在收音机上听到的那些诗,没有其他,他懂得布罗茨基,完完全全地了解他。诗,就有这本事。诗,就是真。可是伦敦的他,布罗茨基却一无所悉。怎么去告诉那冻僵了的人儿,他与他在一起,在他旁边,每日,每天?
约瑟夫.布罗茨基、英娥柏格.芭赫嫚、齐别根纽.赫柏特【注】:他们孤单的筏子,扔在欧洲黑暗的海面上,从那里,他们的诗句释放到空气中,于是沿着广播的电波,这些字句飞入他的小屋,这是他同时代诗人的语言,再一度地告诉他,诗可以是什么模样,也因此告诉了他,他可以是怎么个模样,他心中充满喜悦,竟能与他们居于同一个星球。信号在伦敦收听到请继续发送:要是他可以,这就是他想要传送给他们的讯息。
【译注】Zbigniew Herbert,一九二四︱一九九八,波兰诗人。
在南非时,他已经听过荀白克和贝尔格【注一】作的一两首曲子比方那首弦乐六重奏<升华之夜>。现在破天荒第一回,他又听到魏本【注二】的曲子。关于魏本,曾有人警告。魏本跑得太远太过,他曾读到这种说法:魏本写的已经不再是音乐,却只是随意出现的音。蜷缩着,他听着收音机。一开始先是一音,然后另一音,然后又一音,凝冷如冰晶,串起来如同天上星子。一两分钟痴迷入神之后,曲子便告终了。
【译注一】Alban Berg,一八八五︱一九三五,荀白格的学生。二十世纪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
【译注二】Anton von Webern,一八八三︱一九四五,荀白格的学生,他的管弦乐融合布拉姆斯、Reger及荀白格的调性风格。但后来亦追随苟白格走向无调性。曾担任指挥工作。
魏本在一九四五年被个美国大兵击毙。误会,他们说,战争中的意外。描制出那等乐音的脑袋,那等静默,那等的声音与静默,就这样永远沉寂了。
他跑去看一个抽象表现派的画展,在泰特美术馆。十五分钟之久,他站在一幅杰克森.波洛克【注】的画前,给它机会渗入他,也想让自己看起来颇有鉴赏力的模样,万一有位文雅的伦敦人士,正好瞥见他这个乡巴佬。没用。那幅画对他没产生半点意义。这画有个什么东西,他就是领略不了。
【译注】Jackon Pollock,美国行动绘画(又名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代表作品为:《波西弗依(神话故事)》、《集中》。
隔壁展览室里,高挂在一面墙上,端坐着一幅巨画,画中什么也没有,就只是一团拉长的墨黑,在一片白底之上。 <向西班牙共和国致敬24号>,罗伯特.马哲威尔【注】所作,画旁的说明写着。他深受震慑。这黑色形状,威胁而又神秘,完全把他征服了。似有锣击之声,从画中发出,使他战栗,膝盖发软。
【译注】Robert Motherwell,一九一五︱一九九一,美国画家。着有《达达画家与诗人》。
这份魔力,从哪儿来的呢,这没有定形的形状,和西班牙或任何东西都没有半分相似,却在他里面涌起一股幽暗深沉的感觉?它不美,可是却好像美般向你诉说,霸道专制地说着。为什么马哲威尔能有这股力量,波洛克却没有,梵谷、林布兰也没有?就是那同一种力量吗?那种使得他怦然心动,当见到这个女子,却非另一个女子之时的那种力量吗? <向西班牙共和国致敬>,正对应着住在他灵魂深处的某个什么形状吗?他命里注定的那位女子,又如何呢?她的影儿,也早已深藏在他内心里那股幽暗吗?还要再等多久,她才会现身?当她现身之际,他会已经准备好了吗?
答案到底是什么,他也说不出来。可是他若能以相称的姿态与她相遇,她,那命定的一位,那么他俩做起爱来,将是世间无可比拟之爱,这一点他绝对肯定,那会是一种濒于死亡边缘的狂喜;而待他苏醒归来,将会是一种新我存在,脱胎换骨。电光石火瞬间灭绝,如相对两极之碰触,如双生子之交合;然后,便是缓缓地回苏重生。他一定得为那一刻准备妥当。准备就绪,是一切。
人人戏院安排了萨耶吉.雷【注】电影季。连续几晚,他观赏了阿普三部曲,出神地专心吸收。在主角阿普那苦涩、困陷的母亲身上,在他那迷人、大胆不顾后果的父亲身上,他认出了自己的双亲,带着一种剧痛的罪恶感觉。可是在所有里面,却要数音乐最使他透不过气来,令人昏眩的复杂交错弹奏,在鼓声与弦乐之间,笛声吹奏出的长段咏叹,那音阶还是调式他对音乐的理论知道得还不够多,不能确定是哪一个紧揪住他的心,将他送进一种肉体的郁结,影片结束之后还久久不去。
【译注】Satyajit Ray,印度导演,导有阿普三部曲:《大路之歌》、《大河之歌》、《大树之歌》等。
在这之前,他已从西方音乐里面,尤其是巴哈,找到他所需要的每样东西。如今他却遇到巴哈里面所没有的,虽然也满有它的味道:不是用理性的心灵去理解,却是快活地让步,交由手指的舞蹈接收。
他去唱片行搜寻,在其中一间,竟给他找到一张西塔琴的唱片,乐手叫乌斯达.维拉雅.康【注】,和他兄弟应该是弟弟,从图片上判断弹奏印度七弦琴维纳琴,以及一名未注名的乐手敲塔布拉印度手鼓。他自己没有唱机,不过在店里可以试听最前面的十分钟。所有的感觉都在那儿了:那徘徊不去的音序探索,那颤抖强烈的情绪波动,那狂喜的奔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竟这么好。一个新大陆,而这一切却只要九先令!他把唱片带回小室,夹在两层厚纸板之间放起来,准备哪天可以再听时,好好听它。
【译注】Ustad Vilayat Khan,西塔琴演奏大师。
他楼下住了对印度夫妇。他们有个小婴儿,有时会模糊朦胧地哭叫。他和那男的,在楼梯上擦身而过时,会相互点个头。那女的几乎很少露面。
一天傍晚有人敲门。是那个印度人。他可愿意赏光,明晚和他们共进晚餐?
他接受了,却有几分疑虑。他不习惯那些强烈的佐料。他可以下咽,而不至于喷出吐沫,把自己弄得像个傻瓜吗?
一进门,主人家立刻令他安心了。这家人是从南印度来的;他们是素食者。那些辣味并非印度菜的主要成分,主人解释道:辣味之所以放进菜里,主要只是为了掩饰坏掉的肉味。
南印度食物对味蕾相当温和。真的,果真如此。放在他面前的食物椰子汤加小豆蔻、丁香调味,还有一个蛋卷都百分之百地柔淡。
主人家是工程师。和妻子已经在英格兰有几年了。他们在这里很快乐,他说。他们现在的住处,是目前为止住过最好的地方。房间宽敞,整幢房子又静又有秩序。当然他们不中意英国的气候。可是他耸耸肩有好总有坏,坏的应该一道收下。
他的妻子几乎没加入谈话。她服侍他们吃饭,自己却不上桌,然后便退到角落,小宝宝在那里躺在他的婴儿床里。她的英语不好,她先生说。
他的工程师邻居很钦佩西方的科学、科技,抱怨印度太落后。虽然对机器的讴歌,通常都令他厌烦,他却什么都没说,不与那男人反驳。在英国,这可是第一次有人请他到家中。更何况:他们还是有色人种,他们晓得他是南非人,却依然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他很感激。
问题是,他该怎么做回表谢意?难以想像他也回请他们,夫妻两个而且毫无疑问连同那个会哭的小婴儿,到他在顶楼的房间,吃着纸袋粉泡的汤,而下面一道,如果不是契拉塔辣味香肠,就是乳酪酱通心粉。可是除此,他又能怎样回报他们的款待呢?
一个礼拜过去,他什么动静都没有,然后是第二个礼拜。他越来越觉得难为情。他早上开始听门,等着工程师出门上班,然后自己才步出房门下楼梯。
一定有个什么姿态可以做,某种简单的礼尚往来,可是他却找不着,或者不去找,而且不管怎么说,很快地已经太迟了。为什么,他老是把最寻常、最普通的事,弄成这副德性让自己这么难堪?如果问题的答案是,这就是他的天性,有这种天性,真不知又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改一改自己这种天性呢。
可是,这真是他的天性吗?他怀疑。感觉起来不像是天性,却像是一种病,一种品格上的病:精神上的吝啬、贫薄,跟他对女人的冰冷如出一辙,实质上并无不同。一个人,能从这样一种病中,创造出艺术来吗?如果可以,又显示了艺术到底是什么样的玩意儿呢?
韩普斯德报铺外有个告示牌,他读到一则广告:三缺一找房客,瑞士别业区【注】公寓。自己一间,公用厨房。
【译注】Swiss Cottage,伦敦北区的优良住宅区。
他不喜欢跟人家合住。他比较喜欢自己住。可是只要他继续自己住,就永远不能打破他的隔绝跨出去。他打电话过去,约好时间看房。
招呼他看房间的那个男人,比他大上几岁。留着胡子,穿一件尼赫鲁式蓝上装,前面一排金钮扣。他的名字是米可罗斯,来自匈牙利。公寓很干净,又通风;他要住的那间比他现在租的房间大,装备也比较新式。我要了,他毫不犹疑告诉米可罗斯。我该给你个定洋吗?
没这么简单。留下你的名字和号码,我会把你放在名单上。米可罗斯说。
他等了三天。第四天打电话去。米可罗斯不在,接电话的女孩说。房间?噢已经租出去了,好几天以前就租掉了。
她的声音带有一丝异国的沙哑;无疑她一定很美,有智慧,优雅练达。他没问她是不是匈牙利人。可是如果他租到那间房,他现在就会和她共用一间公寓了。她是谁呢?她叫什么名字?她会是他那位命定的爱人吗,而现在,他的命定却离他而去了吗?谁又是那幸运的一位,有幸得到了那间房,连同原本该属于他的未来。
他有这个印象,那天去看房子,米可罗斯带他看房间时相当敷衍。他只能这样想,米可罗斯是在找一种人,可以为这一室室友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四分之一的房租而已,却是个可以提供愉悦,或风格,或什至浪漫的人。只打量了他一眼,米可罗斯就断定他没有愉悦、风格,和浪漫,就把他否决掉了。
他真应该采取主动。我不是我表面上那样,他当时应该这样说。我看起来也许像个写字员,但实际上我是诗人,或者说将会是个诗人。更何况,我会一丝不苟地付我那份房租,可比大多数诗人好多了。但是他却不曾开口,没有为自己申诉,不管是多么卑微可怜地,为自己、为他的天职请命;而如今,却太迟了。
一个匈牙利佬,怎么有办法搞到间公寓,在时髦的瑞士别业区,还穿一身最时兴的服装,在懒洋洋的早晨迟迟醒来,和一位毫无疑问美貌的,有着沙哑嗓音的女孩,一起躺在床上?而他自己却得在IBM整日做牛做马,住在拱门路旁一间沉闷阴暗的房间?那些打开伦敦欢乐之锁的钥匙,是怎么落入米可罗斯手里的?这些人,是打哪儿找来的钱,供他们过上这种安逸日子的?
他向来都不喜欢不守规矩的人。如果规矩给忽略了,人生就不再有道理了:那还不如干脆,就像伊凡.卡拉马助夫一样,把入场券交回退出吧【注】。然而眼前的伦敦,似乎却尽是些不照规矩来、竟可以逍遥无事的人。他和其他那些他在火车上看到的写字员,深色西服、戴眼镜、苦恼愁烦的写字员,似乎只有他一个傻瓜,笨到死守着规矩不放。那,他又该怎么做呢?他是应该追随伊凡的榜样呢?还是应该学米可罗斯?不管他跟随谁,他觉得,他都会输。因为他没有扯谎、欺瞒,或不守规矩的本事,就像他也没有享乐或作新奇打扮的才能一般。他唯一的本领,就是悲惨、无趣,老老实实的悲惨。而如果这城市,不会给悲惨什么回报,那他待在这儿又是干嘛呢?
【译注】Ivan Karamazov:杜思妥也夫斯基着《卡拉马助夫兄弟》书中主角。书里面伊凡拒绝进入竟会使孩童受苦的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