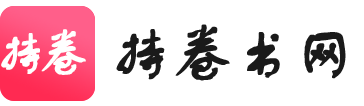一事出有因
在前面四章,我们简要地介绍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三大战役:儒墨之争、儒道之争、儒法之争。这样一种介绍,无疑蜻蜓点水,走马观花,难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甚至以偏代全。但即使如此,也足以让我们顿生敬意,平添仰慕,颇多追思,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同时,我相信大家也都想问:我们民族为什么会涌现出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集中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的思想又为什么会有那么长久旺盛的生命力和永恒的魅力?
这确实值得深思。
不过,要回答前面那三个为什么,还得先弄清一个问题:两千多年前,为什么会出现诸子百家的竞相争鸣,爆发一场历时三百年之久的跨世纪大辩论?
恐怕还得从孔子说起,因为孔子是肇事者。孔子开了一个先例,就是以民间思想家的身分,对天下大事发表意见。此例一开,不可收拾,大家都跟着说起来。墨子说,孟子说,杨朱、庄子、荀子、韩非,都说。老子虽然好像面对着空气,也是说。这就是争鸣,即争着说,而且多半都会提到孔子。所以,秋后算帐,得先拿孔子说事。
何况孔子也是最重要的。正如韦政通先生所言,孔子在先秦时期,便已居于思想史的中心地位,并成为文化思想的代表(《中国思想史》)。这是事实,跟我们喜欢不喜欢没关系。实际上,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目中,孔子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思想家。比如普立兹奖和自由勋章获得者、美国作家杜兰特,在撰写《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一书时,尽管明知可能会引来一些质疑或争论,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孔子列为人类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其余的九位伟大思想家,则依次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阿奎那、哥白尼、培根、牛顿、伏尔泰、康德、达尔文。
然而孔子的问题也不少。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孔子生前并不得志。他东奔西走,四处碰壁;栖栖皇皇,一无所获;哀哀如失群之雁,累累若丧家之狗。这就让人起疑:孔子和他的思想,真有那么伟大吗?如果真有那么伟大,为什么落得如此下场?
这个问题,孔子自己也都想到了。他甚至和学生们进行过讨论。什么时候讨论的?困于陈、蔡之间时(此事我们前面已两次提到,请参看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一节)。据《史记.孔子世家》,当时孔子一行饿得七荤八素,整个队伍人心浮动,连最可靠的学生都忍不住(子路愠见,子贡色作)。孔子自己,也知道学生们有意见、有看法、有怨言(孔子知弟子有愠心),就分别找他们谈话。当然,孔子没找所有的学生,他找的是学生干部,也就是子路、子贡、颜回。谈话的核心内容,就是自己的主张究竟对不对,为什么会走投无路。学生发表了看法,孔子也发表了意见。所以,这三次谈话,很值得玩味。
第一个谈话的是子路。谈话前,照例诵诗。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翻译过来就是:不是犀牛,不是老虎,旷野之上,匆匆赶路。这意思也很清楚:我们既不是犀牛,又不是老虎,怎么跑到这旷野之上,被人围困在这里了?因此孔子接着说:是我们的主张和主义不对吗(吾道非邪)?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吾何为于此)?
先生提出了这样严重的问题,学生当然要回答。于是子路用猜测的口气说:是不是我们还不够仁(意者吾未仁邪),人家并不信任(人之不我信也)?是不是我们还不够智(意者吾未知邪),人家不肯实行(人之不我行也)?孔子说:有这种说法吗(有是乎)?阿由呀,如果一定要别人信任才算仁,那饿死的伯夷、叔齐算什么(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如果一定要别人实行才算智,那被害的王子比干算什么(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显然,孔子并不同意子路的说法,也不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这里。
子路出去后,子贡进来了。孔子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旷野之上,匆匆赶路。是我们的主张和主义不对吗?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子贡说,哪里是先生的主张和主义不对!是先生的主张和主义太伟大了(夫子之道至大也),所以天底下没有地方能够容得下先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接着,子贡用试探的口气说:夫子盖少贬焉?盖,通盍,读如何,何不的意思。所以子贡这话的意思是:先生为什么不降低点身分降点格,不要那么伟大?言外之意也很清楚:那样一来,岂不就有容身之地了?这话孔子也不能同意。孔子说,阿赐呀,一个好农民,能够精耕细作,却未必善于收获(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一个好工匠,能够巧夺天工,却未必尽如人意(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一个君子,能够掌握真理,却未必见容于世(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现在,你不考虑如何掌握真理,只想着怎样才能被别人了解,被别人聘用(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呀,你志向不远大嘛(而(尔)志不远矣)!
子贡出去后,颜回进来了。孔子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旷野之上,匆匆赶路。是我们的主张和主义不对吗?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颜回说,哪里是先生的主张和主义不对!是先生的主张和主义太伟大了(夫子之道至大),所以天下不能容(故天下莫能容)。尽管如此,先生还是努力去推行(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能见容于世算什么(不容何病)?不能见容于世,才显出君子是君子(不容然后见君子)。实际上,不能掌握真理,是我们这些士人的耻辱(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我们掌握了真理,他们不能用,是他们那些当权派的耻辱(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能见容于世算什么?越是不能见容于世,越是证明君子是君子!这下子孔子高兴了。他兴高采烈地说,你们颜家子弟这么有出息吗(有是哉颜氏之子)?你要是钱多,我给你做管家(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这真是妙不可言!颜回和子贡,一个比一个会说话,一个比一个说得好听,却一个比一个不着调,一个比一个不靠谱。比较靠谱的是子路。他的思考是认真的,也是对路的。怎么个对路?怎么个靠谱?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这是战士的思路。一个好的战士,如果打不赢别人,绝不会怪别人太厉害,只会怪自己不争气。他要做的事情,也只有两件,一是练好自己的武艺,二是磨快自己的刀子。子路的思路,就是这样(意者吾未仁邪,意者吾未知邪)。所以,尽管子路并没有找出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下面再说),想法却对路,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可惜,子路的话,孔子听不进去(幸好还没骂他)。看来,从孔子开始,中国人就不善于也不愿意反省自己。
子路是战士,子贡是商人。商人务实。他们做事情,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成交。为了成交,可以让步,这就是讲价。但为了讲出好价钱,又要先抬价。子贡的做法就是这样。他先是帮孔子出价,而且价码极高(夫子之道至大也),然后又建议孔子压价(夫子盖少贬焉)。这是自己和自己讨价还价,目的是成交,即见容于世,被人聘用。可惜子贡的思路和孔子的想法并不完全相同。没错,孔子是想从政,是想做官。所以,当子贡问他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时,他便飞快地一口气说了两个沽之哉(《论语.子罕》)。不过孔子有原则,那就是人可以受委屈,道不能讲价钱。比方说,做不了大官,做小官也对付,但必须行道。道,是不能打折扣的。子贡先是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接着又说夫子盖少贬焉,孔子就怀疑他动机不纯,为成交而成交了。因此孔子教训他,想问题,不能首先想成功不成功,而要想应该不应该。如果不修尔道而求为容,格调是不会高的。
子贡挨这一顿抢白,有点冤枉。因为子贡实在是好心好意,真诚地想帮助老师走出困境。子贡也很聪明,他比子路会说话多了。子路直通通,傻乎乎,上来就在自己这边找问题,孔子怎么会爱听?没挨骂已是万幸。子贡就聪明得多。他先是给孔子吃了一颗定心丸:先生的主张和主义,绝对没有问题。不但没有问题,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哄得老师高兴了,才端出自己的方案。在子贡看来,像他这样先讲大道理,后打小算盘;既务虚,又务实;既有充分肯定,又有整改措施,实在应该是万全之策了。谁知道却碰了一鼻子灰!这就远不如颜回,什么狗屁办法都没有,全是空话,却中了个头彩。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子贡的聪明是小聪明,颜回的聪明才是大聪明。前面说了,子路像战士,所以直言不讳;子贡像商人,所以曲线救国。那么,颜回像什么?像官员,而且是那种特别会和领导打交道的官员。事实上,只有颜回,才真正领会了领导的意图。我们不妨想一想,孔子为什么要提出吾道非邪和吾何为于此这两个问题。是他当真认为自己的主张和主义有问题吗?当然不是。这一点,打死他也不会承认。问题是,这么好的主张和主义,却居然没有一个人采纳和奉行;自己和自己的学生,反倒被困在陈、蔡之间这么个鬼地方。这可不是一句君子固穷,就可以解释,可以交代,可以打发的。这个时候,孔子必须拿出一个说法来,才能带领大家继续前进,不至于作鸟兽散。而且,这个说法还最好是由学生们自己提出来。学生自己说服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鼓励自己,岂不比先生来说教好得多?这就是孔子要找三个学生干部谈话的原因。
谈话的先后也有讲究。司马迁讲得很清楚,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可见谈话的次序,是孔子自己安排的。为什么先和子路谈?因为子路年纪最大,辈分最高,在同学们当中有威望,说话又冲。搞掂了子路,也就一了百了。万一搞不掂,还可以再找子贡和颜回。事实证明,子路并不能真正领会领导意图,他的回答让孔子很不满意。好在孔子原本就没怎么指望他,教训两句,也就算了。
子路指望不上,就只有靠子贡和颜回。为什么先找子贡呢?因为子贡聪明、乖巧,没准有个好说法。可惜这回子贡是自作聪明,他的回答让孔子更不满意。希望变成失望,当然恼火。所以,孔子批评子贡的话,就比对子路说得多,也说得重。所谓而(尔)志不远矣,既是诛心之论,也是恨铁不成钢。
前面这两个学生不得要领,能指望的就只有颜回了。事实上颜回也不负厚望。颜回悟性好呀!我相信他一定琢磨了一个问题:老师为什么要问吾道非邪和吾何为于此?而且,我相信他一定很快就想清楚了:老师绝不会就事论事,局限于这两个问题。为什么不会?因为老师平时教学的时候,就是主张由此及彼、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因此可以肯定:第一,老师并非当真要讨论主义和主张的对错问题。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为什么还要问?需要通过问和答,对自己再做一次肯定。同样,第二个问题也不是问题。为什么不是问题?因为老师的选择,原本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怎么会为吾何为于此而困惑?没有困惑却又提问,那就不是问自己,而是问别人了。问谁?问学生。为什么要问学生?希望学生能够自己想明白。老师其实是在上课呀!老师其实是在做思想工作呀!想明白了这些问题,我们也就不难得出结论:孔子既不需要反思自己(这是子路的失误),也不需要整改措施(这是子贡的失误)。他需要的,只是一个说法,一个既说得过去又能稳定军心,最好还能够鼓舞士气的说法。颜回给出了这个说法,所以颜回受表扬。
但是,颜回的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什么叫越不能见容于世,越证明君子是君子(不容然后见君子)?按照这个逻辑,则所有的君子,就只能是孤家寡人了。这恐怕讲不通。没错,真理是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并不等于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更不等于只要是少数,就一定掌握真理。用走投无路来证明自己掌握真理,说白了是一种自欺。把一切都归咎于外部条件和环境,把责任都推到别人头上,就更是阿Q精神。阿Q怎么说?孙子才画得圆呢!颜回怎么说?小人才处处受欢迎。颜回,岂非阿Q的祖师爷?
所以,颜回得到了孔子的表扬,却也留下了问题,这就是:当我们自己遇到挫折的时候,是应该像子路那样反省,还是应该像颜回这样自欺?我的看法是:反省,肯定正确;自欺,要看情况。因为自欺也不一定就不好,比如身患重病的人,就不妨有意识地自我欺骗。这里的关键是;第一,必须有意识,知道这是自欺。第二,只能自欺,不能欺人,除非需要集体的自欺。比如孔子他们困于陈、蔡之间时,是需要一点集体自欺的。这时,就不能讲逻辑了。当然,孔子组织的讨论,也回答不了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孔子生前四处碰壁,走投无路,究竟是什么原因。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该去问谁?
问孔子的敌人,问孔子的反对派,问那些反对聘用孔子的人,比如晏婴和子西。在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曾经讲到,孔子在齐国被晏婴拆台,在楚国被子西拆台。这些人的反对意见,都记录在《史记.孔子世家》。看看这些意见,或许能弄清问题。
第一件事发生在公元前五一七年,即孔子三十五岁那年。这一年,孔子到齐国找工作,见到了齐景公。齐景公向他问政,孔子回答了八个字,道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了很高兴,说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有的是粮食,我也吃不到嘴里。过了几天,齐景公又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在节财。齐景公又高兴了,准备把尼溪(尼溪)之田封给他。这时,晏婴出来说话了。晏婴是齐国的重臣,说话很管用的。晏婴说了两点。第一,儒者不可重用。第二,礼乐不可复兴。儒者为什么不能重用?也有四个原因。一,能言善辩,巧舌如簧,法制管不了他;二,恃才傲物,自视甚高,上级管不了他;三,崇丧厚葬,劳民伤财,不可以敦风化俗;四,游说诸侯,贪图名利,不可以治国安邦。儒者有这四个问题,当然不能重用。礼乐为什么不可复兴?因为有圣贤才有礼乐。现在,大圣贤不在了,周王室衰微了,礼乐的缺失也已经很久了。再讲礼乐,就不合时宜。然而孔子却装腔作势,不厌其烦。他那一套东西,即便旷日持久也不能穷尽(累世不能殚其学),即便年富力强也不能掌握(当年不能究其礼)。君上如果用它来移风易俗,只怕不是小民的福音(非所以先细民也)。这话齐景公听进去了,于是孔子被打发回国。
第二件事就发生在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时。当时楚昭王不但发兵来解围,还打算封给孔子七百里地。这时,子西出来说话了。子西是楚国的令尹(宰相),说话的份量当然重。子西先问昭王:大王手下的使臣,有比得上子贡的吗?昭王说,没有。又问:大王手下的宰辅,有比得上颜回的吗?昭王又说,没有。再问:大王手下的将领,有比得上子路的吗?昭王又说,没有。又再问:大王手下的官员,有比得上宰予的吗?昭王又说,没有。子西说:当年我们祖先受封于周,不过是个子爵,按规定只能纵横五十里。现在孔丘到处鼓吹恢复周礼周制。照他那一套来做,我们楚国还能堂而皇之地纵横几千里吗?子西还说:想当年,文王在丰,武王在镐,不过百里之地。大王打算封给孔丘的,却是七百里。孔丘得到这么大个地盘,又有子贡、颜回、子路、宰予这样的弟子辅佐,只怕不是楚国的福分。这话楚昭王听懂了(可不能让孔子做周文王,自己做殷纣王),于是不封孔子,孔子也只好又返回卫国。
这就很清楚。晏婴和子西反对孔子,不是因为个人恩怨,而是利害冲突,政见不同。尤其是孔子主张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更使他们不能赞成。子西说得很明白:恢复了周礼周制,楚国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晏婴也说得很明白:那些玩意早就过时(礼乐缺有间),哪里还能移风易俗,治国安邦?孔子的不受欢迎不得志,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孔子要恢复周礼周制,而那些执政者没有一个人赞成;孔子要维护礼乐制度,而那些执政者没有一个人感兴趣。孔子不到处碰壁,才是怪事!
晏婴和子西不喜欢的,也是墨家、道家、法家要批判的。比如《墨子》的《非儒》篇,就记录了晏婴反对齐景公重用孔子的意见,而且话说得更难听,道是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孔丘花言巧语,鼓吹异端邪说,迷惑当世国君;吹拉弹唱,制造文化毒品,残害天下人民。孔子在墨家的笔下,简直成了江湖骗子。
这段话,不见于《史记》,我怀疑是墨子或者其后学借晏婴之口骂孔子(当然也可以怀疑是司马迁故意删去)。这说明墨家对儒家维护的礼乐,已是恨之入骨。不过,墨家不要礼乐,还要仁义(当然内涵不同)。道家和法家,则是连仁义也不要,更不要礼乐。相反,儒家这边,孔子、孟子、荀子,则都要礼乐。因此,以对待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的态度为标准,先秦诸子可以分为两大阵营:儒家与非儒家。儒家维护礼乐,非儒家反对礼乐。只不过,他们反对的原因并不相同,提出的替代方案也不相同。但主张废除礼乐制度,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则是一致的。难怪孔子会成为众矢之的。
如此说来,则儒墨、儒道、儒法这三场争论,又可以归结为同一个问题,即要不要礼乐制度。这就是先秦诸子争论的总焦点。有此焦点,自然因为先前有过礼乐制度;有此争论,则因为礼乐制度正在面临崩溃。也就是说,有礼坏乐崩,才有百家争鸣。于是,我们就又有了三个问题:一,礼乐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二,这种制度为什么会产生并得到实行?三,一个已经实行数百年之久的制度,为什么会面临崩溃?
二以人为本
要回答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恐怕还得先问问:礼乐制度是谁的发明?传统的说法是周公。周公是什么人?孔子经常梦见的人。孔子为什么不梦见别人,老梦见他?因为周公才是周文化和周制度的真正缔造者。据《尚书大传》和《礼记》,周公在他摄政的第六年制礼作乐,结果天下大服。这是周公在取得了军事斗争胜利之后,进行的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有了这两个建设,周政权才稳固了,周制度和周文化也才确立了。孔子经常梦见周公,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周公为什么要创立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
直接的原因,是殷商灭亡的教训。我们知道,武王灭纣,非常之快。联军子月(周历正月)底出发,丑月(周历二月)底就攻进了殷都朝歌,殷纣王就自杀了。一个原本十分强大的政权,怎么说亡就亡了呢?直接的原因,是殷纣王派出去的部队,一到前线就掉转矛头,变成了周武王的先锋。纣王的军队为什么反戈一击?根本的原因,是殷商政权太不把人当人。具体表现也有两个,一是活人殉葬,二是活人献祭。比如江苏铜山丘湾商代社祭遗址中,就同时发现了人骨和狗骨。可见当时是把活人像狗一样,当作牺牲品的。这种特殊的牺牲品,就叫人牲。牲,有两个意思。一是相对于畜,二是相对于牺。动物,养着的时候叫畜,要杀的时候叫牲,合起来叫畜牲。它们用于祭祀,毛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祭祀用人牲,就是把人当牲口,是典型的不把人当人。
用人做牺牲品叫人牲,做陪葬品叫人殉,同样是不把人当人。可是这两种制度,在殷商时代非常盛行。这是既有文献记载,又有考古发现证明的。送上祭坛和埋进坟墓的,不仅有奴隶平民,甚至还有贵族。这也不难理解。因为牺牲品和陪葬品,原本是人神之间进行交易的筹码。出价越高,红利越大。因此,如果是重大祭祀,有特殊要求,或者去世的人物地位特高,光杀战俘和奴隶就不够意思,非杀贵族不可。比如纣王的大臣比干,我怀疑就是因此而被杀,或者以此为借口杀的。
然而,尽管殷商政权杀了那么多的人,甚至杀了贵族来祭祀,来陪葬,皇天上帝还是不保佑他们。相反,他们还亡得很快。显然,周人要想保住胜利果实,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殷的统治者既然不把人当人,那么,周的统治者又该怎么办呢?
也只有一种选择:把人当人。
把人当人,这就是仁,也就是人其人。据《尚书.泰誓》(也写作太誓),周武王在伐纣之前,曾发表宣言,说惟人万物之灵,说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意思是有再多的亲戚,也不如仁爱人民)。周武王是不是真说过这话,难讲。但要说周人有这种观点,大约是实。范文澜先生甚至说,周人是废除了人牲制度和人殉制度的,而且认为这件事具有重大进步意义(《中国通史》)。当然,一种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制度,说废除就废除了,并不可能。事实上此后的人牲和人殉,也史不绝书。不同的是:这两件事已不像在商代那样被认为理所当然。相反,谁要再搞,还会遭到抵制和批评。
这是有证据的。比如公元前六四一年,宋襄公与曹国、邾国的国君会盟,让邾文公杀鄫国的国君(子爵)祭祀社神,司马子鱼就反对。据《左传.僖公十九年》,司马子鱼说:用大牲口来进行小祭祀,尚且不可(小事不用大牲),哪里还敢用人(而况敢用人乎)?子鱼还说:祭祀,原本是为了人(祭祀以为人也)。人,是神的主人;神,是人的客人(民,神之主也)。用人做牺牲品,谁能够享用(用人,其谁飨之)?你们这样倒行逆施,只怕没有好结果。将来能够善终,就是万幸(得死为幸)!遗憾的是,子鱼的反对似乎并没有成功,那个倒楣的鄫国子爵还是被杀了。 《春秋》经文的记载,是邾人执鄫子,用之。
好在也有反对成功的,只不过这回反对的是人殉。据《礼记.檀弓下》,齐国的大夫陈子车死于卫国,他的老婆(妻)和管家(宰)就商量着要用人殉葬,而且连要杀的人都定下来了。为什么要用人殉葬呢?老婆和管家的理由是:夫子死在卫国,生病的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所以应该派两个人到阴间照顾他(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然而陈子车的兄弟陈子亢(亢音刚)反对。陈子亢说,用人殉葬,不合礼法(以殉葬,非礼也)。当然了,你们也有你们的道理,我哥哥生病的时候莫养于下(养,去声,音样)嘛!不过,最该照顾他的,也就是二位(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所以,我的意见是:能够不用人殉葬,最好(得已,则吾欲已)。实在不行,就只好杀你们两个(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结果大家也能想像,是陈子车的老婆和管家都不再坚持人殉。
其实陈子亢这个人,大家应该能够想起来,他就是《论语》中曾经向子贡和孔鲤提问的陈亢(请参看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我称之为编外粉丝的那个。现在看来,陈亢虽然是编外粉丝,却也得孔子真传。因为孔子也是反对人殉的,而且连用俑都反对。俑,音勇,也就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比如秦始皇墓中的兵马俑。对于这类东西,孔子深恶痛绝。据《礼记.檀弓下》,孔子曾明确表示为俑者不仁;而据《孟子.梁惠王上》,孔子的话说得更难听,道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我们知道,发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为了代替人。与用人殉葬相比,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杨伯峻先生认为,是孔子不知道这个过程,以为用俑在前,用人在后。有了俑殉,就会有人殉。我倒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孔子是从根本上反对人殉。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用真人、活人固然不行,用假人,用俑,也不行。因为俑是人的替身,也是人的象征。用俑殉葬,就是承认用人殉葬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何况当时的俑,都做得活灵活现,某些木俑还能踊动,这才叫做俑。所以孟子认为,孔子反对用俑,就因为它们太像人了(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礼记.檀弓下》也说,用这样酷似真人的俑殉葬,与用人简直没有区别(不殆于用人乎哉)!故此例不可开,此风不可长。此例一开,人殉就有复辟的可能,因此连这个口子也必须堵住。显然,这是一种原始的、素朴的人道主义精神。其核心,就是要把人当人,不能把人当牲口。子鱼的态度,子亢的想法,孔子的观点,都如此。
问题是,仅仅把人当人远远不够。为什么不够?因为天命不可废,鬼神不可无。天命为什么不可废?废了天命,周的政权就没有了依据。鬼神为什么不可无?没了鬼神,周的统治就没有了手段。灭商之后,武王也好,周公也好,都一再对别人说:我们为什么要取代殷商?我们为什么能取代殷商?就因为有皇天上帝的授权。这就叫天命。天命,原来是给夏的。但是,后来上天改主意了,授权给商,让他们灭夏,这就叫革命,即殷革夏命。这回也一样,是我们接受上天的授权,革殷商的命,即周革殷命。这就是西周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天命还得讲,鬼神还得要,祭祀和丧葬还得搞,又不能再像殷商那样不把人当人,那又该怎么办?
也只有一个办法:把神当人。
这个想法,恐怕也来源于周公。周公这个人,曾经先后生活于文王、武王和成王三个时代,亲身经历了周民族的兴起(文王时代)、胜利(武王时代)和建设(成王时代),感触非常之多,体会也非常之多。这些感触和体会,有的记录在《尚书》,有的记录在《诗经》。比如《诗.大雅》中的《文王》,据说就是周公的作品。在这首诗里,周公提到了一件事,就是周革殷命以后,殷商的那些贵族,都穿着漂漂亮亮的礼服,毕恭毕敬排着队,在周人的祭祀仪式上行礼。于是周公说,天命真是伟大呀!殷商的子孙不也上亿吗?还不是统统变成了周的臣属,参加我们的祭祀?此时此刻,他们心中想念的,究竟是谁的祖宗呢?
我猜,周公是亲历过此事的。而且,这凄楚哀婉的一幕,看得他瞠目结舌、胆战心惊!谁能保证我们周人,就不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因此,他在赞美天命伟大的同时,也痛感天命靡常(《诗.大雅.文王》)。看来,天,并不总是只保佑某一个民族、某一个政权。瞬息之间,可能就转移了。所以,周公对召公奭说: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 (《尚书.君奭》)也就是说,天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能做的,就是谦虚谨慎,兢兢业业,把文王和武王的美德继承下去。否则的话,那老天爷可是翻脸不认人!
周公的这些话,代表着周人在胜利之后的反思。其中表现出来的理智和冷静,令人惊叹!他们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反倒惊竦恐惧于天不可信和天命靡常。天命无常,靠得住的就只有德;天不可信,信得过的就只有人。当然,天命还在,天意还有,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说到底,还是看人的表现。
因此,周公和他的同事,还有他的追随者,包括许多代以后的追随者们,便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策,或者说采取了一种高明的策略:神还要敬,命还要讲,皇天上帝也还要拜,但对于天、神、命,以及它们与人的关系,必须重新解释,重新定位。怎么解释?怎么定位?三点。一,人与天的关系,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就是说,皇天上帝并不一定认准了只保佑某个民族、某个政权。谁有德,就保佑谁。二,人与神的关系,是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就是说,鬼神明察秋毫,人做好事他们就赐福,人做坏事他们就降灾。三,人与命的关系,是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就是说,命运本身无所谓好坏,全看人们自己的选择。你选择好,就是福;你选择坏,就是祸。是福是祸,自己看着办。
这样一来,人与天、人与神、人与命的关系就全都变了,而且是越来越不把村长当干部,不把豆包当干粮,也就是越来越不把天、神、命当回事。事实上,说天惟德是辅,还多少承认上天选择的主动权;说神依人而行,这种主动权就打了折扣;而当他们说命运惟人所召时,主动权就完全在人手里了。于是,以神为本,就变成了以人为本;神的祭坛,也就变成了人的舞台。而且,越到后来,人就越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鬼神也就越是被边缘化。这样,发展到春秋晚期,就有了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什么叫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说,鬼神还是要祭祀的,但犯不着上杆子巴结。正确的态度,是敬畏鬼神,同时疏远。
显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孔子究竟相信不相信鬼神的存在?我看其实不信。如果信,那就应该亲而近之,为什么要敬而远之?但是,鬼神是否存在,搞不清,也讲不清。最好的办法是存而不论,挂起来。问题是鬼神可以不讨论,祭祀却仍然要进行。既然要祭祀,就必须信神信鬼;但要相信鬼神,又实在缺乏证据。不能信,又不能不信,怎么办?好办得很!祭神祀祖的时候,权当他们存在好了。这就是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这不是老奸巨猾,而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在孔子看来,人之所以要祭神祇,祀祖先,无非是表达一种心意和敬意罢了。既然是表达心意和敬意,那就必须假设他们存在,认为他们存在,权当他们存在,而不要去问他们是否当真存在。比方说,我们祭祀祖先时,祖先还在吗?当然不在,但又活在我们心里。对待神,也如此。
孔子的这个主张,无疑非常明智,所以他才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也。其实这种明智也是必然。道理很简单:把人当人,就不能把神当神;不把神当神,就只能把神当人。最后的结果,则必然是不再讨论鬼神的有无。因此,这是一种理性态度,也是一种人文精神。其核心思想,就是认为现实的人和人生,比搞不清也说不清的鬼神重要。鬼神存在如何,不存在又如何?要紧的还是自己如何。这是人道主义,更是理智态度。或者说得再明白一点:把人当人,就是人道主义;把神当人,就是理智态度。
这就当然是以人为本了。不过这样一来,却又有了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你可以反对某种信仰,但不能没有信仰;可以不要某种崇拜,但不能没有崇拜。为什么不能没有?因为在人类的早期,包括人类文明的早期,所有的民族都得靠它们或他们凝聚族群。比方说,炎黄时代靠图腾,殷商时代靠鬼神。显然,周人只能用某种信仰去取代另一种信仰,用某种崇拜去替代另一种崇拜,不能取消崇拜和信仰。因此,在把神拉下神坛的同时,还必须把别的什么送上去。那么,他们又该怎么办?
说来很简单:把人当神。
这倒也不难理解。既然崇拜是必需的,那么,不崇拜神,就会崇拜人。问题是人也有好几种,周人崇拜谁?他们选择的是圣人。什么是圣人?一般地说,圣人都是历史上对我们民族起过大作用的人。他们往往同时也是过去的领袖(王),因此也叫先王、先圣。最早的,有伏羲、神农、黄帝;晚一点,有尧、舜、禹;再晚一点,有商汤、周文。不过,圣人并不一定是王。比如周公、孔子,就圣而不王。王也不一定是圣人。比如夏桀、殷纣,就王而不圣。王不一定圣,圣不一定王,怎样才算?两条,一是有大贡献,二是有大发明。比如大禹治理洪水,商汤推翻暴政,是大贡献;周公制定礼乐,孔子创立儒学,是大发明。当然,最好是既有大贡献,又有大发明,比如伏羲发明了八卦,神农发明了医药,黄帝发明了车船。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理应受到崇拜。早期的圣人,就是这样。他们是在我们民族历史上开思想、文化、制度之先河的人。他们留下的言论,就是经;他们创立的制度,就是典;他们阐述的思想,就是道。圣人,掌握了真理(道),创造了经典(文化、制度),改变了生活,因此叫圣。从周代开始,我们民族崇拜的,就是这样一些历史上或者传说中曾经存在过的人。儒家有此崇拜,墨家和道家也有,只不过名单不同(比如墨家崇拜大禹,道家崇拜伏羲)。实际上,圣人的名单并不固定。比如孔子,原本不是圣人的,后来是了。再后来,孟子等等,也都是了。再后来,关羽也是了,孟子则一度被拉下来。可见谁是圣人,有争议。要崇拜圣人,没问题。
这就不是神的崇拜,而是不折不扣的人的崇拜,因此应看作以人为本的组成部份。问题是:圣人虽然是人,享受的待遇却是神。他们不容亵渎,不容诽谤,不容非议,与神没有两样。比如魏的嵇康,就因为离经叛道非薄圣人,被司马昭杀了。当然,司马昭杀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只是原因之一,甚至只是借口。但能做借口,也说明问题。同样,司马昭杀嵇康虽然是在魏的景元三年(公元二六二年),圣人崇拜却是周人开的头。没有周人崇拜圣人之前因,就没有司马昭杀嵇康之后果。没错,嵇康之前,也有批判圣人的,比如庄子和韩非。不过他们只是批判某些圣人,不批判圣人的全部。何况那是在战国,礼坏乐崩了,圣人也就不圣。礼不坏乐不崩的时候,有人批判吗?没有。没有倒也不是不敢,而是因为在周代,圣人其实是被当作神来崇拜的。圣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很高,没人会去批判。所以,圣人崇拜,就是把人当神。
不过这里还是有问题。什么问题?当作神的,不一定非得是圣人嘛!比如英雄,不能崇拜吗?当然能。然而中国人的英雄崇拜,远不能与圣人崇拜相比。比方说,追日的夸父,射日的后羿,无疑都是英雄。但是,他们能跟伏羲或者尧舜比吗?不能。后世也一样。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刘备、孙权,都是英雄。可是人们崇拜的,却是诸葛亮和关羽。诸葛亮和关羽是什么人?圣人。圣人的地位高,还是英雄的地位高,不是一目了然吗?
于是我们要问:周和周以后的中国人,为什么最崇拜圣人呢?还是得弄清楚究竟什么是圣人。孟子的定义,是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也就是人群当中最有道德的。比如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各不相同。伯夷清高(圣之清者),伊尹负责(圣之任者),柳下惠随和(圣之和者),孔子识时务(圣之时者),但又都是圣人(《孟子.万章下》)。为什么?因为都是道德楷模。这是所谓后圣。回过头再看先圣: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哪一个不是有德之君?这就叫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第三梯队的孔明、关羽、岳飞等等,也如此。他们能够成为圣人或者候补圣人,都首先是因为有道德,比如诸葛亮鞠躬尽瘁,关羽义薄云天,岳飞精忠报国。
这就清楚了。原来要成为圣人,有贡献、有发明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要有道德。圣人,一定是众望所归的道德楷模,这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首要条件。显然,中国人的所谓圣人崇拜,其实不过是道德崇拜。所以,如果说把人当人体现的是人道主义,把神当人体现的是理智态度,那么,把人当神体现的就是道德精神。人道主义、理智态度、道德精神,这三条合起来,就叫以人为本。
问题是,这与我们要讨论的礼乐制度又有什么关系呢?
三好大一个家
以人为本与礼乐制度有什么关系?关系就在于,礼乐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文化。文化比制度重要,文化精神又比文化方式重要,正如立法精神比法律条文重要。礼乐制度的精神是什么?第一条就是以人为本。为什么是以人为本呢?因为所谓礼乐,是周人创造的不同于夏制度和商制度的新制度,也是不同于夏文化和商文化的新文化。而区别开夏商周三种文化的,首先就是这一条。过去,人们总把夏商周简单地看作三个朝代。其实,夏商周不仅是三个朝代,也是三个时代,更是三个民族和三种文化。准确地说,是三个不同的民族在三个不同的时代,先后创造了三种不同的文化。这三种不同的文化,有着三种不同的精神。简单地说,就是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礼记.表记》)。尊命,其实就是信天命。尊神,其实就是敬鬼神。尊礼,其实就是重人事。所以,这三种不同的文化,也可以各有一个关键词:天命、鬼神、人文。周文化既然是人文文化,当然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要把人当人、把神当人、把人当神。这就有了圣人崇拜。圣人是人,同时又是最有道德的人。所以,崇拜圣人,其实就是要以德治国。这就是礼乐制度的第二个内容,也是礼乐文化的第二种精神,而且是核心内容和核心精神。也就是说,以人为本是前提,以德治国是核心。所谓礼乐制度,其实就是围绕这个核心来设计的。
那么,周公他们又为什么要以德治国?
两个原因。一是殷商的教训,二是统治的需要。殷商为什么灭亡?不把人当人。这就是失德。周人为什么胜利?把人当人。这就是有德。这一点,周人心里应该是有数的。据说,武王伐纣的时候曾经对联军说:纣王那边虽然人多,可是离心离德。我们这边虽然人少,却是同心同德(《尚书.泰誓》)。由于《尚书》的《泰誓》篇来历不明,这话并不能肯定是武王说的,却能代表周人的观点:失德者失天下,有德者得天下。更何况,为了解释政权的合法性,周人还一再宣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也就是谁最有德,谁就能得到皇天上帝的授权。以前,夏桀失德,商汤有德,天下就归了商人。现在,殷纣失德,周王有德,天下自然就归周人。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当然也就必须以德治天下。总之,无论是吸取教训,还是维护统治,周人都必须主张并实行以德治国。
然而以德治国是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道德这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怎么治天下?因此,还要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来辅助,来做支撑点,这就是礼乐。为什么是礼和乐?这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礼,什么是乐,它们又各有什么作用和功能。
先说礼。
什么是礼?说法很多。我认为,周公制礼作乐的礼,是一种制度。什么制度?等级制度。这一点,举个例子就能说明。什么例子?五服。五服这玩意,中国人都知道,又未必都清楚。出了五服,就不是亲戚,这个大家都知道。但,为什么出了五服就不是亲戚?这个管着是不是亲戚的制度为什么叫五服?不一定明白。
其实五服是一种礼,也是一种制度。什么制度?丧服制度。什么叫丧服制度?就是家里死了人,怎么穿衣服。怎么穿呢?五种穿法,五个等级。最高的一级,叫斩衰。衰,音崔,上衣。上衣叫衰,下衣叫裳。斩衰,就是最粗糙的上衣。怎么粗糙?第一,必须是生麻布;第二,必须是粗麻布;第三,裁剪的时候不能用剪刀,只能用刀砍,所以叫斩衰;第四,不缝边。这种衣服,搁在今天就是酷,搁在当时却是苦。正因为是苦,所以是最高规格。什么人穿呢?主要是三种人:臣为君、子为父、妻为夫。另外还有一个特例,就是父为嫡长子。嫡长子为什么有此特权?后面再说(请参看下一节)。
斩衰以下,还有四个等级:齐衰(读资崔)、大功、小功、缌麻。共同特点,是都用熟麻布,也都缝边。因为缝边,所以叫齐衰。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麻布的粗细。齐衰最粗,大功次之,小功又次,缌麻最细。实际上,所谓缌麻,就是细麻布。不过,齐衰再粗,也粗不过斩衰。斩衰的用布,是又生又粗,面料和做工都最差。这就是等级,也是规格。下面列出表来,大家一看就明白:
第一等(斩衰):生麻布,最粗,刀砍,不缝边;
第二等(齐衰):熟麻布,次粗,裁剪,缝边;
第三等(大功):熟麻布,较粗,裁剪,缝边;
第四等(小功):熟麻布,较细,裁剪,缝边;
第五等(缌麻):熟麻布,最细,裁剪,缝边。
由此可见,规格越高,穿得就越差、越苦。为什么?丧服嘛!不差不苦,不足以表达悲痛之深。所以,丧服的规格越高(也就是穿得越差越苦),服丧的期限也越长。第一等,斩衰,三年(实际二十五个月)。第二等,齐衰,或三年,或一年,或五个月,或三个月,看对象。第三等,大功,九个月。第四等,小功,五个月。第五等,缌麻,三个月。五服的等级,就表现在这三个方面:布料的好坏、做工的粗细和时间的长短。面料好坏不同,做工粗细不同,丧期长短不同,适用的对象也不同。也列一张表,同样一看就明白:
第一等(斩衰):三年,臣为君,子为父,妻为夫,父为嫡长子;
第二等(齐衰):三年,父已去世子为母,母为嫡长子;
第二等(齐衰):一年,父未去世子为母,夫为妻,孙为祖父母;
第二等(齐衰):五个月,为兄弟、众子、叔伯父母、曾祖父母;
第二等(齐衰):三个月,为高祖父母;
第三等(大功):九个月,男子为堂兄弟,女子为亲兄弟,公婆为嫡长子之妻;
第四等(小功):五个月,为堂祖父母、外祖父母、舅舅、姨;
第五等(缌麻):三个月,为族人、岳父母、外甥、外孙、女婿。
于是我们要问,搞这么复杂,干什么呢?
体现差异。要知道,礼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规定等级和差别,叫礼辨异(《礼记.乐记》)。具体地说,就是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比方说,同为祖辈,就要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姥爷姥姥)。爷爷奶奶死了,服齐衰(第二等),丧期一年。外公外婆去世,服小功(第四等),五个月。为什么?内外有别,父系为内,母系为外。所以,父系为堂(堂兄、堂弟、堂姐、堂妹),母系为表(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堂,还在家里;表,则在外面。因此,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堂兄妹不能结婚,表兄妹就可以(比如贾宝玉与薛宝钗或林黛玉),还很提倡,叫亲上加亲。这就是别内外。
为什么要别内外?为了定亲疏,即父系为亲,母系为疏。所以,就连表亲也还要再分,分为姑表和姨表。姑表,是父系之亲;姨表,是母系之亲。于是姑表亲于姨表。那么,舅舅、姑父、姨父,谁又最亲?对不起,舅舅第一,姑父第二,姨父第三。这个等级秩序是怎么排出来的?看亲疏。舅舅是母亲家的人,与母亲同姓。姑父和姨父,则既不是父亲家的人,也不是母亲家的人,与父母亲都不同姓。结果,舅舅理所当然排第一。姑父和姨父,虽然都是外姓人,但姑姑是父系,姨姨是母系,只好委屈姨父排第三,让姑父排第二。这笔帐,很好算。但是,舅舅和姑姑,哪个面子大,就不好说了。为什么?姑姑是父系,舅舅是母系。这样看,姑姑面子大。问题是,姑姑是女人,舅舅是男人,又该怎么说?传统的办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看事情,二看辈分。一般地说,国事问舅舅,家事问姑姑。家事当中,涉及父系的问姑姑,涉及母系的问问舅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舅舅的面子再大,也大不过姑奶奶,因为姑奶奶辈分高。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祖辈当中,除了祖父母,就数姑奶奶面子大。如果是老姑奶奶,那面子就大得吓人。因此,一个女人,如果厉害非常,我们就会叫她老姑奶奶或者小姑奶奶。
由此可见,决定等级差别的,除了血系,还有辈分。这就不但要别内外,还必须序长幼。比如父亲去世,服斩衰(第一等),三年。儿子死了,服齐衰(第二等),只有五个月。这就是长幼有序。序长幼的目的是明贵贱,即长贵幼贱。不过,长幼只是贵贱的标准之一,此外还有男尊女卑、君尊臣卑。比如君主死了,臣子要服斩衰,这就是君尊臣卑。又比如丈夫死了,妻子服斩衰(第一等),三年。妻子去世,丈夫却只服齐衰(第二等),一年。这就是男尊女卑。尊卑,是最重要的标准。
又是尊卑,又是贵贱,又是内外,又是亲疏,如此这般地排列组合下来,就是五服。这五个等级当中,最高一级,是君主、父亲、丈夫、嫡长子。他们不是至亲(如丈夫),就是至尊(如君主),或者兼而有之(如父亲)。最低一级,则是族人、岳父、岳母、外甥、女婿、外孙。他们或者没有血缘(如女婿),或者关系疏远(如族人),所以排在第五等。五等之外,没有规定,就不算亲属或亲戚了,叫出了五服。很清楚,贯穿五服的原则,就是十六个字: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
这就是礼。它的核心,就是等级和秩序。有了这一系列的等级,整个社会就条理分明、秩序井然,因此叫伦。阐明这个秩序的原理,就叫伦理;体现伦理的法则,就叫礼法;体现伦理法则的制度,就叫礼制;体现伦理法则的情感,就叫仁爱。儒家主张仁爱,反对兼爱,原因就在这里。孔子一再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认为执政之要首在正名,原因也在这里。
问题是,秩序为社会所需,等级却不符合人性。人,生而平等,没有人愿意做人下人。森严的等级,严格的规定,肯定让人不舒服、不高兴、不爽。何况周人的这些规定,也未必都合理。我们知道,五服制度有一个精神,就是越亲就越近,等级也越高;越疏则越远,等级也越低。因此,父亲去世,服斩衰(第一等),三年。祖父母去世,服齐衰(第二等),一年。曾祖父母,也是服齐衰,五个月。高祖父母,也是服齐衰,三个月。这是有道理的,亲则近,疏则远嘛!但是,父母亲,同样是最亲近的人,却不一样。父亲去世,肯定服第一等的斩衰,三年。母亲去世,却看情况。父亲不在世,三年。父亲在世,一年。而且不管是三年还是一年,都服第二等的齐衰。这就是不平等。还有,祖父母二等,外祖父母四等,岳父岳母五等,也明摆着是不合理,不平等。这也不仅仅是五服的问题。所有的礼制,都有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估计周公他们也清楚。那么,他们有解决的办法吗?
有。什么办法?既制礼,又作乐。
作乐,为什么就能解决问题呢?这就要看什么是乐。乐,有两个读音,也有两个意思。一个音岳,就是音乐。一个音勒,就是快乐。这两个意思,是相通的。为什么会相通?因为听音乐是快乐的。因此,快乐的生活,美好的社会,也应该像音乐。音乐是什么样的?是和谐的。为什么和谐?因为由不同的乐音所构成。乐音有四个不同:音高、音长、音强、音色。每个音和每个音,都不一样。有的音高,有的音低,有的音长,有的音短,但是组织在一起,很好听。这就是和谐。为什么?多样统一。
礼乐制度的创造者认为,我们的社会,也应该这样。比方说音乐有宫商角征羽,爵位就可以有公侯伯子男,丧服也就可以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嘛!五服和五爵就像五音,是等级,也是秩序。至于谁是公谁是侯,谁是伯谁是子男,就像宫商角征羽,也像谁是老爹谁是儿子,全是天意,没有价钱好讲。要紧的,是所有的乐音,都安分守己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不要乱动。不乱动,就和谐。和谐又怎么样呢?就心情舒畅,听音乐一样快乐了呗!
这当然有道理,不过同时也有问题。什么问题?不同的乐音组合在一起,安排得好,当然和谐。但安排不当,也很难听的。然而周人却告诉大家毋庸置疑,因为礼乐制度是周公制定的。周公是什么人?圣人。圣人做的事情,还会错吗?所以,周公设计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周公安排的社会,就是最好的社会;周公谱写的乐曲,就是最好的乐曲,大家照着演奏跟着唱就是,有什么可着急的呢?
如此说词,倒也头头是道,问题是管不管用。现在看来,作用还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音乐有三大功能:宣泄功能、调节功能和情感传达功能。一个人,心里不痛快,站在黄土高坡上吼一嗓子,没准就舒服了。这就是宜泄功能。格罗赛的《艺术的起源》说,一位探险家在澳洲吃了当地禁食的贻贝,他的土著向导只好在黑夜里恐怖地歌唱直到睡熟。这就是调节功能。因此,完全可以用乐来进行心理调节,弥补礼的不足。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情感的传达。所谓传达,就是让他人、让欣赏者也体验到相同的情感。这其实也是一切艺术的功能。事实上,当时的所谓乐,并不只是音乐,而是包括了一切艺术,其中最主要的是诗和舞蹈。 《礼记.乐记》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情深,就是情意深长;文明,就是文采鲜明。情意既深长,文采又鲜明,当然能够让人体验到相同的情感。体验到相同的情感又怎么样呢?就心心相印,息息相关,同心同德了。这样一种相同的情感,平时可以帮助人们和平共处,战时则可以促使人们同仇敌忾。比如《诗经》中的《无衣》,我怀疑就是秦国的一首军歌。它的歌词是这样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话翻译成白话,就是:谁说你没有军衣?我和你共一件战袍。君王就要发兵了,修理好我的长矛,我和你同一战壕!对于这首诗,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但我以为只要不是假道学和书呆子,都不难从中体验到一种强烈的情感,一种慷慨激昂的战斗豪情。我们知道,上古时代的诗,是可以歌唱的;那时的歌,也是可以舞蹈的。因此,当秦王和他的子民们载歌载舞的时候,大约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吧!因为那统一的旋律、统一的节奏和统一的动作,只能导致统一的感受和统一的行动。
这就叫乐统同(《礼记.乐记》)。乐统同,礼辨异,这就是礼乐最主要的作用和功能。也就是说,礼,是用来辨别差异、区分等级的;乐,则是用来统一情感、保证和谐的。礼与乐,是一个和谐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
礼与乐的这种关系,有点像太极图中的阴阳二鱼,相反、相依、互动,又同在一个圆圈内,围绕同一个圆心。这个圆心,就是德。因为周公之所谓乐,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音乐,而是有德之乐。它们的目的也不是娱乐,而是表现伦理情感,进行道德教育。只不过,这种教育又是很快乐的,这就叫寓教于乐。这样的教育,就叫乐教。乐教与礼教合起来,就叫礼乐教化。礼,保证行为符合道德;乐,保证情感符合道德。行为和情感都符合道德,以德治国的方针,就落到了实处,这就叫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礼记.乐记》)。也就是说,以德治国,礼乐辅之,一个核心(德),两个支撑点(礼与乐),这可真是煞费苦心。
现在,我们大体上明白什么是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了。简单地说,就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在这种制度下和文化中,社会是有等级的,同时又是无矛盾的,就像音乐。看来,周公是把他们的天下和社会,看作合唱团了。合唱团当然要有不同的声部,高音部、中音部、低音部等等。所以,在周公及其追随者看来,一个音乐般美好的和谐社会,也应该有不同的等级。这话貌似有理,其实不通。没错,合唱团里是有不同声部。但这只是分工的不同,绝不意味着不同声部的人在人格上不平等。事实上,在音乐作品中,乐音并没有音格问题。不同的乐音之间,也不存在音格的不平等。如果不平等(比如规定低音只能短而弱,高音必须长而强),音乐就不会和谐,也不会好听。由此可见,不平等的社会绝不可能和谐。真正和谐的社会,应该是人人平等又各有所需,各有所长,各得其所。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不过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周公他们用礼乐来实施统治,实在算得上是既开明又高明,因为这比血腥镇压、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好多了。事实上,思想上确立以人为本,政治上实行以德治国,制度上推行礼乐教化,这一系列的举措,都说明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民族,这才创造出如此精巧高明的新制度和新文化。这也正是春秋战国时期会出现诸子百家争鸣的第一个原因心智的成熟。
当然,这只是第一个原因。它还有第二个原因,即社会的剧变。社会剧变的具体表现,就是礼坏乐崩。这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直接原因。于是我们就要问:如此煞费苦心创造出来的制度和文化为什么会出问题,又为什么会面临崩溃?
四命运呼叫转移
要知道礼乐制度为什么会崩溃,先得弄清楚它为什么能实行。为什么能实行?因为家天下。什么叫家天下?就是把整个天下看作和说成一个巨大的家族。它有一个最大的族长或家长,叫天子。这个巨大的家族下面,又有百十来个次大的家族,叫国。它们也都有各自的族长或家长,叫诸侯,也叫国君。每个次大的家族下面,是若干中等的家族,叫家。它们也都有各自的族长或家长,叫大夫,也叫家君。再下面,则是最小的家族,甚至小家庭。它们的族长或家长,叫士。士,是大夫的儿子或兄弟;大夫,是诸侯的儿子或兄弟;诸侯,大部份是天子的儿子或兄弟,小部份是其他人。不过这些其他人,也多半是天子的舅舅、外甥、女婿之类。因此,士家族是大夫家族的分支,大夫家族是诸侯家族的分支,诸侯家族则是天子家族的分支。总之,普天之下,都是一家子。这就可以实行礼乐制,也必须实行礼乐制。为什么?因为家人之间,一是要相亲相爱,这就是仁;二是要互帮互助,这就是德;三是要长幼有序,这就是礼;四是要其乐融融,这就是乐。可见,礼乐制能够实行,是因为天下一家。
或许有人会问:西周时的天下,范围已经很是不小,比如周在陕西,燕在河北,晋在山西,楚在湖北,宋、卫在河南,齐、鲁在山东。此外,湘、赣、苏、浙,也都有周的诸侯国。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民,怎么能变成一家子呢?
周人的办法,是宗法制加封建制。什么叫宗法制?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一个家族众多的子女中,确定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老三的制度。谁是老大?嫡长子。谁是老二、老三?次子和庶子。什么叫嫡长子?父亲与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什么叫次子?父亲与正妻所生的其他儿子。什么叫庶子?父亲与侧室(妾)所生的儿子。次子和庶子,无论年龄大小,出生先后,其地位与嫡长子都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只有嫡长子,才代表着家族的血统,叫正统。家族的爵位和财产,也原则上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叫嫡系。正统和嫡系叫大宗,次子和庶子叫小宗。因此,嫡长子去世,就连父亲都要为他服斩衰,此为五服中长幼颠倒的唯一例外。这就叫嫡长子制,是宗法制的核心。
问题是,这种制度,与家天下制又有什么关系呢?周人的说法是这样的:首先,设定周王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所以叫天子。如此,则诸侯是天的次子或庶子。这就确定了天子与诸侯的宗法关系。依此类推,诸侯是国族的嫡长子,大夫则是国族的次子或庶子;大夫是家族的嫡长子,士则是家族的次子或庶子。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大夫与士,都有宗法关系,岂非天下一家?
不过,光有宗法关系,还不行。因为宗法关系是社会关系,只能用于家庭、家族。周王国(姬姓)与宋公国(子姓)、齐侯国(姜姓)、郑伯国(姬姓)、楚子国(芈姓)、许男国(姜姓)之间,却是国家关系。这就还必须封建。什么叫封建?就是假定皇天上帝把天下交给了周王,周王又把天下分成若干国,各自指定一个国君去统治,这就叫封土建国,也叫封邦建国。具体地说,划定疆域叫封,指定国君叫建。国君得国以后,也不能独吞,还要再分一次,分给本国的大夫。周王分土地和人民予诸侯,叫建国;诸侯分土地和人民予大夫,叫立家。大夫立家以后,就不能再封建了,但可以给士食田。食田,就是吃赋税的田地,也就是给饭吃。士的食田是大夫给的,大夫的采邑是诸侯给的,诸侯的领地是天子给的,这就是封建。
封建制和宗法制加起来,结果是什么呢?是天子、诸侯、大夫、士之间,都有两重关系。第一是宗法关系,即嫡庶。具体地说,天子是嫡,诸侯是庶;诸侯是嫡,大夫是庶;大夫是嫡,士是庶。第二是封建关系,即君臣。具体地说,士是大夫的臣,大夫是士的君,也是家中所有庶民的君,叫家君。大夫是诸侯的臣,诸侯是大夫的君,也是国内所有国民的君,叫国君。诸侯是天子的臣,天子是诸侯的君,也是天下所有人民的君,叫天下共主。也就是说,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大夫与士,既是君臣,又是家人。是君臣,就要讲尊